時間:2023-06-02 09:22:55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收入證明樣本,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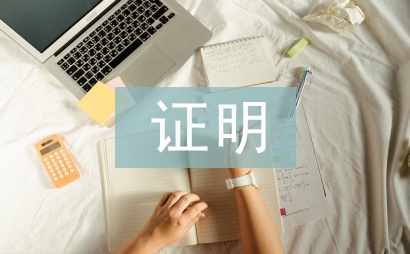
茲證明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系我司員工,職務______________。買房貸款工作證明信樣本
xx-xx年年收入為:
xx-xx年年收入為:
年收入包含年薪、獎金、提成、及各項補貼,個人所得稅已由單位代扣代繳。買房貸款工作證明信樣本
某某單位(公章)
年 月 日
精選貧困生證明書 家庭經濟困難證明(樣本) 茲有我鎮(縣)××××××(具體地址)村民(居民)×××、×××之子(女)×××在××××××××大學就讀。該生家庭××××××××(家庭主要成員狀況),主要從事××××××××(主要收入來源),家中經濟收入×××××××××××××××××××(年家庭收入狀況),經濟狀況××××(是否困難),家庭經濟能力無法負擔該生在校的學習和生活費用。請有關銀行和學校給予該生助學資助,扶助該生完成學業。
特此證明!
××××鄉(鎮)人民****(或縣民政局)
助學貸款貧困證明格式
貧 困 證 明
茲有我鄉(鎮)(居委會等)×××(父母親姓名)之子(女)×××(學生姓名),于××年××月考入貴校學習。由于×××原因(每個家庭的具體原因),導致家庭經濟困難,希望學校、銀行能為其提供國家助學貸款,幫助其順利完成學業。
×××鄉(鎮)人民****(公章)或×××居委會等(公章)
××年××月××日
1、貧困證明中要求明文出現貸款人名字,并且要求與本人身份證上的名字完全一致,不能用同音字、不規范簡寫字代替,不能有錯別字。貸款人名字不得涂改。
2、貧困證明要求加蓋家庭所在地鄉(鎮)人民****公章,或更高一級主管部門公章。其中有效的公章有:鄉(鎮)人民****、縣民政局、市民政局。城市居民可以是居委會、街道辦事處、社區公章。注意村民******的公章無效、單位公章無效。貧困證明盡量不出現兩個或以上公章。
3、貧困證明中明文出現“家庭經濟困難,需要申請國家貸款”字樣。
4、貧困證明要求用材料紙或文稿紙,且用鋼筆或水性筆書寫,用圓珠筆書寫無效。
證明茲證明某學生是我們縣某村的學生,其家庭生活非常貧困,父母(把工資收入之類的介紹一下)如常年務農,沒有固定收入,或者說下崗之類,年收入不足3000元。家里還有兄弟姐妹什么的,比如在上學,年齡小,都介紹一下。特此證明。單位地址年月日蓋公章
家庭貧困證明
家庭經濟困難證明(樣本) 茲有我鎮(縣)××××××(具體地址)村民(居民)×××、×××之子(女)×××在××××××××大學就讀。該生家庭××××××××(家庭主要成員狀況),主要從事××××××××(主要收入來源),家中經濟收入×××××××××××××××××××(年家庭收入狀況),經濟狀況××××(是否困難),家庭經濟能力無法負擔該生在校的學習和生活費用。請有關銀行和學校給予該生助學資助,扶助該生完成學業。
特此證明!
××××鄉(鎮)人民****(或縣民政局)
助學貸款貧困證明格式
貧困生證明
茲有我鄉(鎮)(居委會等)×××(父母親姓名)之子(女)×××(學生姓名),于××年××月考入貴校學習。由于×××原因(每個家庭的具體原因),導致家庭經濟困難,希望學校、銀行能為其提供國家助學貸款,幫助其順利完成學業。
凡準備申請助學金的新生,來校報到前須在本人戶口所在地相關部門開具家庭經濟困難證明,一式兩份,具體辦理如下:
一、農村戶口新生只需攜帶《家庭戶口薄》戶主頁(首頁)和本人頁復印件各二份即可辦理。
二、城鎮戶口新生(選其一辦理):
1、享受“城市低保”家庭的新生,可攜帶《城市居民低保證》復印件和戶口薄戶主頁及新生戶籍頁復印件;
2、其他新生,需在社區委員會按以下三類原因開具證明:
(1)長期疾病類
(2)單親家庭類
(3)父母下崗類
家 庭 經 濟 困 難 證 明
茲有 (家庭戶口所在地首頁內的具體地址)居民 (爸爸或媽媽姓名)之子(女) (學生姓名)被xx學院錄取,該生家庭主要成員 有 (爸爸、媽媽、兄弟姐妹姓名),主要從事 (主要收入來源如種植、工資、買賣生意、低保金、退學金等),家中收入 元(家庭年收入狀況),家庭經濟困難,開支大,負擔重,望相關部門給予該生在校期間的生活補助,資助其順利完成學業。
特此證明
(村委會或居民委員會)經辦人簽字:
根據我國目前的情況,1996、1997和1998年之間,凈資產收益率在10%區域集中的上市公司均達到上市公司總數的20%,甚至更多。這些上市公司具有相當大的操縱凈收益的嫌疑,因此筆者選取這類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數據,包括資產負債表數據和利潤表數據分別進行財務指標特征的分析。
一、研究的方法和反映操縱手段的財務指標的選擇
筆者借鑒國外對失敗企業和收購及被收購企業的財務指標特征的研究方法,針對有操縱利潤嫌疑的企業,設計出財務指標特征分析的步驟如下:第一,根據理論常識分析凈資產收益率受到人為操縱的企業其可能的操縱手段,然后選擇與操縱手段相對應可能受到影響的財務指標。第二,按照特定的標準選取作為對比研究所需要的標準企業。第三,計算出可能存在利潤操縱的企業以及作為對比的標準公司各個財務指標的平均值。第四,將兩類企業同一個財務指標的平均值進行對照,觀察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第五,為了排除因個別極值無法刪除,或統計樣本內部的數據比較分散對統計結果的干擾,筆者同時采用“十分法”對各樣本的全部數據進行排序,直接觀察各樣本數據在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的分布狀況,比較兩組數據在分布上的差異。“十分法”的原理是,將樣本的數據按照由小到大的順序進行排列,然后找出樣本中每十個百分點的數量位置所對應的財務指標,10%位置的財務指標數值表示有10%的企業該財務指標值低于該數值,而90%的企業該財務指標高于該數值,以此類推。每相鄰的兩個十分點位置上的財務指標表示有10%的企業該財務指標數值分布在這兩個數值之間。最后,對得出的統計結果進行解釋。
根據近年來一些研究人員的研究發現和對企業可能采取的操縱凈收益指標的手段的分析,企業可能采取以下提高凈資產收益率的手段,并且這些手段可能導致相應的一些財務指標出現異常:
1、通過非營業活動提高凈利潤。包括諸如出售資產、出售投資、改變投資的核算方法等提高營業外收入或投資收益等活動。為避免所得稅率差異對分析的影響,筆者選用營業外收入占利潤總額的比重、投資收益占利潤總額的比重和營業利潤占利潤總額的比重三個財務指標。營業利潤占利潤總額的比重越高,說明企業靠經營正常業務取得利潤的比例越高,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企業的凈收益的質量較好;由于投資收益和營業外收入較易受到人為的操縱,因此這兩部分的比例越大,企業凈收益指標被認為操縱的可能性越大。如果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利用非正常經營業務調整利潤的現象,則從總體上看,這些企業的營業外收入或投資收益占利潤總額的比例可能會較一般公司高一些,而營業利潤占利潤總額的比例相對低一些。
2、通過虛假銷售、提前確認銷售或有意擴大賒銷范圍調整利潤總額。這些銷售無法取得現金,因此當企業出現這些現象時,應收賬款的占用就會增加,表現在財務指標上,一方面體現為應收賬款占流動資產的比重增加,另一方面還可能體現為應收賬款周轉率的減小。如果這種方法成為企業普遍采用的調整利潤的方法,從總體上看,這類企業的應收賬款占流動資產的比重就會高于一般企業,而應收賬款周轉率則會低于一般企業。
3、對已經發生的費用或損失推遲確認。當企業采用推遲確認費用或損失時,企業掛賬的費用就會上升,導致資本化的費用比例升高,例如待攤費用、遞延資產、無形資產以及類似的其他長期資產。如果人為操縱凈收益的企業普遍存在利用推遲確認費用或損失的做法,與這些資本化費用有關的財務指標就有可能出現異常,如待攤費用占流動資產的比重、無形資產及其它資產占流動資產的比重等可能會給我們一些提示。
4、利用關聯交易調整利潤。如果這種現象在操縱凈資產收益率的企業中比較普遍,就會在這些企業的關聯交易額占銷售收入或銷售成本的比例上體現出差異,并且應收賬款中關聯方的應收賬款比重較大。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對關聯交易披露的不規范性,投資者較難從財務報表和報表附注中采集出關聯交易的詳細數據,因此筆者根據為調整利潤進行的關聯交易通常不使用現金的特點,選擇分析其他應收款指標占流動資產比重的指標。其他應收款體現企業與正常經營業務無關的有關各方的資金往來,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映企業與關聯方的資金關系,比如出售投資給關聯方后應收回的款項等。其他應收款占流動資產的比例大,說明企業與關聯方可能存在比較密切的聯系,利用關聯方調整利潤的可能性也較大。
二、研究數據的選取
筆者采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上市公司資料庫》光盤中數據作為研究對象,從中篩選出1996、1997和1998年凈資產收益率在10%區間,即[10%,11%]之間的公司作為樣本(簡稱10%區域的公司)。同時,根據這些公司所處的行業和規模,在凈資產收益率相對受到人為干擾小一些的公司中尋找對照研究所需的相同數量的標準公司樣本,舍去個別實在無法找到對照的標準公司,以保持兩個樣本最大程度的可比性。通過查找和比較,筆者選取的單個樣本數量如下表所示:
缺乏數據和刪除的公司數量合計不到總數量的15%,并且樣本數量遠遠大于統計中要求的大樣本標準(30個),因此可以認為研究的結果基本代表了所有凈資產收益率在10%區域的公司狀況。
三、統計結果
筆者統計出的1996、1997和1998年凈資產收益率在10%區域的公司和用于對比的各標準公司的資產總額以及八個財務指標的調整平均值、平均值差異的檢驗值見下面的表格。比較資產總額的目的在于證實兩個樣本是否存在規模差異。調整平均值是在刪除了5%的極值之后計算出的各樣本的資產規模和財務指標的平均值。同一年度內凈資產收益率在10%區間的上市公司與標準公司財務指標平均值差異的檢驗值代表了平均值差異的大小,當該檢驗值超過1.64時(筆者使用的是單尾檢驗),我們就有95%的把握認為平均值確實存在這種差異,因此,認為該差異是顯著的。當該檢驗值低于1.64時,我們就認為在統計意義上這種差異不明顯,我們不能以95%的把握性確定這種差異是否真的存在。在樣本的方差較大時,通過統計檢驗有時難以確定平均值差異的顯著性,利用十分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這種不足。
財務指標差異及其顯著性統計結果
根據上表顯示的統計結果以及筆者進行的“十分法”排序的結果,1996年到1998年各年度10%區域上市公司和一般公司各個財務指標之間的差異情況見下表:
注:“顯著”指通過平均值差異的檢驗發現存在明顯差異;
“有區別”指在平均值差異的檢驗中不能證明存在明顯差異,但利用“十分法”排序可以看出存在明顯差別;
“無區別”指不論在平均值差異的檢驗還是“十分法”排序中都看不出明顯存在差別。
資產總額的比較結果證明,有操縱凈資產收益率可能的公司與標準公司之間不存在規模差異,筆者的研究的確已經排除了規模對其它財務指標的影響。從上面的統計結果看,在選取的八個可能反映企業利潤操縱的財務指標中,只有無形資產占總資產比重以及營業外收入占利潤總額的比重兩個指標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差異,其他六個財務指標均在不同程度上體現出10%區域上市公司與一般公司的差別。
四、研究結論
1、財務指標中體現的上市公司利潤操縱手段。
通過對可能存在利潤操縱的上市公司和一般公司財務指標的比較,我們認為以下操縱利潤的手段在上市公司中有普遍性:
(1)通過非營業活動提高企業利潤。筆者對凈資產收益率在10%區域的上市公司樣本中營業利潤占利潤總額比例最低的企業數據進行了調查,結果令人吃驚。1996年的94家樣本公司中有6家公司該指標出現負數,1997年166家樣本公司中有3家該指標出現負數,而1998年160家樣本公司竟然有7家公司該指標出現負數。這些負數意味著這些公司的營業活動是虧損的,也就是說,他們達到10%的配股線居然完全依靠營業外的經濟活動!
(2)通過增加投資收益提高利潤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在1996年和1997年的統計結果中,我們發現10%區域的上市公司投資收益占利潤總額的比重遠遠高于標準公司,1996年差異達八個百分點,1997年差異達四個百分點。利用投資收益操縱利潤在個別公司達到極其嚴重的程度,在10%區域的上市公司樣本中,投資收益占利潤總額100%以上的企業1996年有6家,1997年有2家,1998年有3家,這意味著這些達到配股最低標準的上市公司創造10%的凈資產收益率竟然完全依靠投資收益!
(3)采用與關聯單位進行交易提高利潤。筆者不能直接證明這些關聯交易的內容,但是其他應收款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上市公司與關聯方聯系的緊密程度,這使我們不能不猜測這些關聯方對企業利潤的影響。1997年和1998年10%區域的公司其他應收款比重的明顯異常說明這些公司從事非正常經營活動的行為十分普遍,而且交易經常采取非現金形式。筆者統計了樣本中10%區域的上市公司其他應收款占流動資產比重超過50%的公司數量,1996年,該數目為4家,占樣本的4.3%,1997年為11家,占樣本的6%,1998年為9家,占樣本的5.6%。這些公司竟然有一半以上的流動資金占用在非正常經營活動之上!
如果筆者對其他應收款的多少代表與關聯方聯系的緊密程度猜測沒有錯誤,其他應收款多的上市公司很可能在經營活動上也存在與關聯方的緊密聯系。雖然筆者沒有考察關聯交易引起的上市公司經營活動收入和利潤的增加,但1997年和1998年,10%區域上市公司同時都出現一定程度的應收賬款占流動資產比重比標準公司偏高、應收賬款周轉率比標準公司偏低的現象,這與我們看到的其他應收款比重的異常在時間上存在一致性,由此我們有理由懷疑上市公司通過關聯交易既操縱非營業利潤,又操縱營業利潤。
(4)通過人為擴大賒銷范圍或采用提前確認銷售、甚至搞虛假銷售增加營業利潤。在1997年和1998年,10%區域上市公司的應收賬款占流動資產比重比標準公司偏高,以及應收賬款周轉率的偏低,說明比起標準公司,10%區域的上市公司更多地記錄了非現金形式的銷售業務。鑒于筆者統計時采取了控制行業和控制公司規模的方法,由于行業和規模導致的應收賬款規模和回收速度的差異就被排除在外,剩下的原因只能用不正常來說明。這種不正常,一是可以用上面提到的關聯交易來解釋,另外就是用擴大賒銷范圍、提前確認銷售、搞虛假銷售等原因來解釋。
除上述具有普遍性的利潤操縱手段外,還具有兩種不具有普遍性的利潤操縱手段,即通過費用資本化影響利潤和通過提高營業外收入影響利潤。
2、上市公司操縱凈收益手段的改變。
連續考察1996年到1998年10%區域的上市公司出現異常的財務指標,我們發現各年中這些財務指標的變動不盡相同。也就是說,在不同年度,由于種種原因,上市公司采用的操縱利潤的手段偏好有所不同。
(1)1996年,平均值差異檢驗證明存在明顯差異的財務指標有投資收益占利潤總額的比重和營業利潤占利潤總額的比重;考慮十分法排序的結果,其他應收款占流動資產的比重也存在差異。其他指標差異則不明顯。可見,在這一年中,企業普遍采用增加投資收益的手段提高利潤,而虛增收入、利用關聯交易調整利潤的做法還不十分普遍和明顯。
(2)1997年,平均值差異檢驗證明存在明顯差異的財務指標有:待攤費用占流動資產的比重、其他應收款占流動資產的比重、投資收益占利潤總額的比重以及營業利潤占利潤總額的比重;考慮“十分法”排序的結果,應收賬款占流動資產的比重和應收賬款周轉率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這一年中,企業普遍采用多管齊下的方式提高利潤,包括增加投資收益、利用關聯交易、虛增銷售等。
(3)1998年,平均值差異檢驗證明存在明顯差異的財務指標只有其他應收款占流動資產比重和應收賬款占流動資產比重;考慮“十分法”排序的結果,應收賬款周轉率也存在差異。而以前出現過差異的待攤費用占流動資產比重、營業利潤占利潤總額的比重以及投資收益占利潤總額的比重幾個指標差異不明顯。可以認為,這一年中企業普遍采用的調整利潤的手段集中在虛增銷售或關聯交易上,而對利用投資收益增加利潤的做法不再特別感興趣。
五、研究結果的啟示
雖然筆者的研究對象是凈資產收益率在配股最低限以上臨近區域的上市公司,但是研究所發現的財務指標與利潤操縱手段上存在的聯系具有普遍性,可以幫助我們在各種情況不辨別利潤操縱。研究證明,盡管我國上市公司人為操縱凈資產收益率的手段各有不同,但他們在操縱利潤的同時,其他財務指標卻能夠暴露其操縱手法,因此,只要我們能夠對這些反映利潤操縱的財務指標給予足夠的關注,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識別上市公司的操縱手段,去偽存真,得到企業真實的獲利水平。通過以上的研究,我們得到以下一些啟示:
首先,凈收益或利潤總額有關的指標表現企業真實盈利能力存在嚴重缺陷。這些指標中包含了與企業正常經營無關的、缺乏穩定性的一次性收益內容,如投資收益和營業外收入,以及在本文中沒有涉及的財政補貼等,這些項目隨時會由于企業達到目的而消失。用這些指標評價企業,將給投資者帶來巨大的風險。從前面的統計中我們看到,標準公司營業利潤占利潤總額的比例明顯高于可能操縱利潤的上市公司,因此相比凈資產利潤率或總資產報酬率,營業利潤受到利潤操縱的干擾較小,利用營業利潤計算的有關指標相對穩定,對表達企業的實際盈利能力會更加有用。
其次,在操縱凈收益的手段中,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通過投資收益增加利潤。投資者應對利潤表中的投資收益給予非常的重視。對于投資收益占利潤總額比重較大的企業,應該仔細分析投資收益的來源,辨別這種投資收益的長久性。如果一次性的投資收益,比如出售投資所得的收益數量較大,這種投資收益的長期性就很難保證。
第三,其他應收款是我們應該給予足夠重視的資產負債表項目,一些企業可能沒有披露關聯交易或關聯方關系,但其他應收款項目的性質實際上會告訴我們這些企業與其他企業或單位之間的非常關系,所以其他應收款的多少可以幫助我們判斷該上市公司受到其他企業或單位的影響程度,這種影響越大,該上市公司的凈收益指標的可靠性越差。
關鍵詞:上市公司;地理分部;重要性;
中圖分類號:F23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7)05―0092―04
一、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在10%的重要性水平的運用上,現在至少存在兩種不同的意見:一是以FASB為首的代表在1997年修訂分部信息準則時主動放棄了該標準,轉而規定了應予披露的分部個數最大數量不應超過10個;二是以IASB為首的代表則一直秉承按10%的重要性測試水平來確認分部,并同時規定了應予以披露的分部個數最大不超過10個。而我國早在1997年證監會的《準則第二號》的修訂稿中,就明確規定了行業分部的披露標準以10%為限,2000年、2002年和2006年財政部相繼了《企業會計制度》、《企業具體會計準則――分部報告(征求意見稿)》和《企業具體會計準則――分部報告》,非常明確地指明了分別按照分部收入、分部收益或分部資產10%的標準來披露符合條件的備分部。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披露是否嚴格按照該標準來確認分部,而且10%的標準是否能夠用于區分具有不同風險和收益的分部,在《企業會計制度》前后和《征求意見稿》前后的披露實務是否得到明顯改善,以下將就這些問題進行討論。
按照我國確認分部的10%標準,只要分部收入、分部收益或分部資產分別占所有分部相應總額10%或者以上的部分才能確認為一個報告分部。與證監會的《準則第二號》相比,如果企業嚴格按照《企業會計制度》和《征求意見稿》中有關分部確認的初衷去確認,其確認的條件就被放寬了,它不僅可以按照分部收入占所有分部相應總額10%的標準來確認,而且還可以按照分部收益或者分部資產分別占所有分部10%的標準來確認分部。根據以上的解釋,在《企業會計制度》和《征求意見稿》后,企業應予以披露的可報告分部的個數將會增加,而小于10%的分部的數量將會下降。由此,得到以下假設:
H1:假設分別按照分部收人、分部收益或者分部資產分別占所有分部相應總額的10%的重要性標準來確認地理分部,那么,企業所披露的大于等于10%的可報告分部的個數將增加,而小于10%的分部的個數將下降,分部信息的透明度將得以提高。
(二)樣本選擇
由于在檢驗時需要分別要求以分部收入、分部收益或者分部資產為依據來判斷公司所披露的大于或等于10%和小于10%的分部平均個數,并考慮其逐年的變動趨勢,因此,該樣本的選擇需要考慮到逐年披露了分部收入、分部收益或者分部資產等信息的情況。根據中國披露分部信息的實際情況,由于分部確認標準的擴大直到2001年財政部《企業會計制度》時才予以體現,在《企業具體會計準則――分部報告(征求意見稿)》(2003)中,對于分別按照以上三個標準來確認分部的方法更進一步明確。因此,為了確認分部的平均個數的變動趨勢需要2001~2003年的數據。將2004年的年報剔除在外,是因為2003~2004年并未出現關于分部信息披露規范變動的任何決定,而且經過統計分析其分部披露信息并未改變。另外,為了與以前所確認分部的標準相比較,也需要2000年的數據,但是根據以前的研究發現,在各公司2000年年報中披露了分部資產的公司是微乎其微的,而為了保持樣本的可比性、連續性與有效性,以下分析以“2002年財富中國100強”的公司為樣本(因為這些公司在2000~2003年的相應數據比較完整)。
這100家公司分別在國內、國外市場上市的公司各有76家和22家,但在國外上市的公司并不需要遵守中國的會計準則,因此,為了考核中國分部信息披露中的10%的重要性測試水平的合理性,下面以遵守我國會計準則的公司為樣本。這樣,本研究樣本為76家在國內上市的公司,其中有4家公司為銀行(因為銀行的主要業務與一般的制造企業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本樣本將其除掉),另有2家公司沒有披露任何分部信息,綜合起來,本研究中的有效樣本為70家。為了考慮《企業會計制度》和《征求意見稿》前后有關地理分部確認實務上的改進問題,需要這70家樣本公司2000~2003年相關數據的變化趨勢。
二、研究結果
(一)所確認的地理分部研究
1.樣本公司2000~2003年逐年所披露的地理分部個數分析。將70家樣本公司分別在2000~2003年的平均可報告地理分部的個數進行統計,經過統計,樣本公司分別以分部收入、分部收益、分部資產為依據所披露的分部個數如表1所示。
由表1統計結果可知,2000~2003年分別依據分部收人、分部收益或分部資產等指標所確認的地理分部中大于或等于10%的可報告分部以及小于10%的披露分部的平均個數呈逐年增長的趨勢。但在2000~2001年以分部收入所確認的大于或等于10%的地理分部的平均分部個數稍微有下降,其地理分部的平均個數依次為2.5,2.313,2.043。從整體上說,分部個數的逐年增加說明了分部信息披露的詳細程度不斷加強,這不僅給信息使用者提供了較多與其決策相關的信息,而且便于提高分部信息的透明度。
根據以前的研究,我國直到2001年才開始強制性地要求符合條件的各上市公司披露分部資產的信息(聶萍,2005),在2000年及以前披露分部資產信息的公司更是鳳毛麟角。經統計,這些樣本公司中,2001年披露了分部資產項目的公司16家,其中只有6家公司的分部資產信息是在地理分部中給予披露的。盡管對于分部資產的披露還剛剛起步,但是以分部資產為依據來確認的分部個數是不斷增長的,以分部資產為依據所劃分的大于或等于10%的可報告地理分部均值在2000~2003年間依次為2.13,3.25,3.25。
總之,分部信息披露深度和廣度兩個層面上的增加表明了分部信息在相關性上得到顯著改進,分部信息透明度得到提高。
2.樣本公司2000--2003年所披露的地理分部個數的變動趨勢。下面將2001年與2000年和2003年與2001年這兩個期間的各地理分部的分部數均值進行進一步比較,并經均值檢驗予以分析,借以探明10%標準的合理性,主要數據見表2。
在地理分部的確認中,除了以分部收入所確認的大于或等于1096可報告分部均值在2001~2000年和以分部收益為基礎所確認的分部個數在2001~2003年是顯著減少之外,分
別以分部收益、分部資產來劃分的大于或等于10%可報告分部在2000~2001年是顯著增加的(P分部收入2001~2000=0.000;p分部資產2001~2000=0.000),而小于10%的披露分部個數在2000~2003年是顯著地增加的(p分部收入2003~2001=0.005;p分部收益2001~2000=0.000;p分部收入2003~2001=0.003;p分部資產2001~2000=0.000;p分部資產2003~2001=0.001)。分部個數的增加表明了分部信息披露深度的逐步增強,這說明了分部信息披露制度的實行對于改善地理分部信息的披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地理分部在增加分部資產項目披露的同時,減少了以分部收益和分部收入等為依據來確認的分部個數,這說明分部信息披露廣度上的增長是以減少披露深度為代價的,在分部信息披露的詳細程度和披露的廣度上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均衡。
(二)地理分部的進一步考察
可報告地理分部平均個數的變化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其披露實務上的改進,同樣也可能反映其經營活動的一些變化,特別是與近期縮小企業規模或增加企業產業集中度有關(Comment,R.&Jarrell,G.A,1995)。因此,為了仔細考察公司分部信息披露實務上的改進,排除公司縮小規模壓力對分部個數變動的影響,尤其是10%重要性標準的運用對地理分部信息質量的重要作用,有必要按照公司管理層披露分部信息的意圖及有關披露規則進行進一步考慮。按照以上的思路充分借鑒C.R.Emmanuel,N.W.Garrod&C.McCal-lum,E.D.Rennie(1999)的相關研究,并立足于我國資本市場的相關數據,將地理分部進一步分為以下三組:(1)自愿披露組。該組表示在2001年的年報中不僅披露了分部收入和分部收益,還主動披露了分部資產的公司。(2)同時披露了分部收入和分部收益組,該組表示在樣本期間同時披露了分部收入和分部收益的公司。(3)非充分披露組。該組表示在樣本期間或者披露了分部收入或者分部收益的公司。每組按照公司的披露實際情況,將各公司所披露的可報告分部分為大于或等于10%的可報告分部組和小于10%的披露分部組。其具體樣本公司數分別為6、40、24,具體地理分部的均值以及樣本期間各組均值變化如表3和表4所示。
從表3、表4可知,其各組均值以及均值變化的結果有如下特點:
(1)對于自愿披露組,以分部收入、分部收益為依據所劃分的大于或等于10%的可報告分部和小于10%的披露分部平均個數在2000~2003年出現為負的變化,而以分部資產為依據所劃分的大于或等于10%的可報告分部和小于10%的披露分部個數的均值在2000-2003年是增加的,而且大于或等于10%和小于10%組可報告分部均值在2000~2001年還-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P大于或等于10%分部資產2001~2000=0.017,P分部資產2001~2000=0.073),這說明了在自愿披露組中由于額外披露了分部資產項目的內容而使以分部收入、分部收益所確認的分部平均個數減少了。
(2)對于披露分部收入和分部收益組而言,以分部收入、分部收益為依據所確認的大于或等于10%可報告分部和小于10%的披露分部個數的均值在2001~2003年是顯著減少的,其中:P大于或等于10%分部收入2003~2001=0.001,P分部收入2003~2001=0.000,P大于或等于10%分部收益2003~2001=0.000,P小于10%分部收益2003~2000=0.000
而在2000~2001年同時,以分部收入和分部收益為依據所確認的大于或等于10%的可報告分部和小于10%的披露分部的平均個數是增加的,但都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而且以分部收益和分部收入所劃分的大于或等于10%組的變動幅度小于10%組的變動幅度,2003~2001年則反之。
(3)對于非充分披露組,以分部收入為依據劃分的大于或等于10%的可報告分部和小于10%的披露分部個數均值在2000~2003年是顯著減少的:P大干或等于10%分部收入2003~2001=0.000,P小于10%分部收入2001~2000=0.0000而以分部收益為依據劃分的大于或等于10%的可報告分部和小于10%的披露分部平均個數在2000~2003年是顯著增加的:P大于或等于10%分部收益2001~2000=0.000,P大于或等于10%分部收益2003~2001=0.002,P小于10%分部收益2001~2000=0.042,P小于10%分部收益2003~2001=0.000
(4)自愿披露組中,雖然自愿披露了分部資產信息,但同時使以分部收入和分部收益為標準所確認的分部均值下降,說明了對于地理分部而言,分部信息披露廣度上的增加卻限制了披露深度上的擴展。在非充分披露組中,10%標準的運用使披露的廣度有所加強,但披露分部收益的均值增加是以分部收入中的可報告分部明顯減少為代價的,因此,該組中同樣存在分部信息披露廣度和深度上的均衡問題。披露收入和收益組中,同時以分部收入和分部收益為基礎所確認的分部均值在2001~2003年是減少的,而且當大于或等于10%組的減少幅度比小于10%組的減少幅度要小的時候,似乎表明管理層出于分部信息劣勢競爭成本的影響而運用10%的重要性標準,將那些較小的地理分部合并成為一個較大的卻毫無組織的部分,從而避免將更多的分部信息報告給外部。而且并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各組中大于或等于10%組的變動幅度超過了小于10%組的變動幅度,因此,H1無法得到充分的證明。
三、研究結論及建議
地理分部披露廣度和深度上的均衡表明,目前中國多元化上市公司對于運用10%標準作為確認重要性分部披露依據時,更多地只是準則字面上的遵從,而且在運用該標準時由于缺乏標準的上限,導致在地理分部的運用上出現了更少更大的廣義概念,10%重要性測試的運用對于改善分部信息披露質量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為了提高地理分部信息披露的有用性,有助于信息使用者正確決策,對于地理分部的披露有必要在以下方面作出改進:
l重要性標準的選擇問題。并不存在太多的理由認為采用10%作為判斷重要性的數量標準是合理的,而且并不能證明5%或15%的標準就是不合適的(shahrokh,1993)。重要性標準的選擇將以能幫助信息使用者去理解公司不同風險和收益的內涵為標準,在考慮采用數量標準的同時,應考慮質量標準來劃分重要分部。改變以不同國家或地區,同一國家不同行政區域作為分析單元的狀況,而且加強地區分部披露與年報其他部分的一致性,以提高地理分部信息的透明度(Nancy B.2000)。
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綜觀現有的盈余管理計量方面的相關文獻,盈余管理的實證計量方法主要包括三種類型:應計利潤分離法、具體應計利潤法以及盈余分布法。盈余分布法通過分析確定企業可能實施盈余管理的閾值點,然后檢驗閾值處密度函數光滑或連續性來判斷企業是否在閾值點實施盈余管理。在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實施收購時,管理層會利用資本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和會計監管制度的不完備性實施盈余管理,由于各家實施MBO的上市公司盈余水平存在顯著差異,因此,很難合理確定一個閾值點以檢驗上市公司管理層是否實施盈余管理。特定項目應計法適合特定行業的某一項或一組應計項目。而實施MBO的上市公司涉及多個行業,并且需對可能實施盈余管理的多個應計項目進行分析檢驗。因此本文的實證研究不適合采用盈余分步法和特定項目應計法。本文采用應計利潤分離法進行實證研究。應計利潤分離法采用模型將應計利潤分離為可操縱應計利潤(DiscretionaryAccruals,DA)和不可操縱應計利潤(Non—DiscretionaryAccruals,NDA),并用可操縱應計利潤來衡量盈余管理的大小和程度。Kaplan(1985)指出會計中權責發生制的本質是應計利潤(非操控性應計利潤)會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而改變,因此在對非操縱性應計利潤的計量中應考慮經濟環境的改變對企業應計利潤產生的影響。在利用應計利潤分離方研究盈余管理的模型中,只有瓊斯模型及其衍生的模型明確地將經濟環境改變引入到對非操縱性應計利潤的估計中。
Dechow,Sloan&Sweeny(1995)、Guay,Kothari&Watts(1996)、Thomas(2000)等對應計利潤分離法相關模型進行實證分析表明,瓊斯模型和修正的瓊斯模型的實證研究結果相對較為可靠。而陸建橋(1999)、陳小悅、肖星和過曉燕(2000)、夏立軍(2003)的研究則證明,在中國證券市場上,瓊斯模型和修正的瓊斯模型同樣較為適用。考慮到中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行為李清(2008)、吳連生(2007)、王婷等2009、張雷2009,而瓊斯模型假設銷售收入不會縱的可能性較低,因此,本文采用修正的瓊斯模型對上市公司管理層收購的盈余管理進行分析。修正的瓊斯模型如下:TA=NI一CFO(1)式中,TA。表示應計利潤總額,NI表示凈利潤,CFO.表示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這三個指標均為經過第t—l期期末總資產調整后的第t期數值。TA產l(1/A_1)+僅2l(AREV.一AREC)/A『-1j+3(PPECAl_1)(2);NDA=僅1(I/A1)+2l(AREV一AREC.)/A_1j+3(PPE/A}-1)(3);DA.=TA一NDA(4)式中,NDA表示經過第t一1期期末總資產調整后的第t期的非操控性應計利潤,DA表示經過第t一1期期末總資產調整后的第t期的操控性應計利潤,AREV。表示第溯和第t一1期的收入差額;AREC。表示第t期和第t一1期的應收賬款的差額;PPE表示第t期期末的固定資產價值;A表示第t一1期期末總資產;、:、0【表示公司特征參數,可以運用估計期各項數值進行回歸取得。根據修正的瓊斯模型,本文先采用配對公司的相關數據通過式2估計參數d、Q、僅,,然后將估計出的參數帶人式3,采用樣本公司相關數據計算出樣本公司的非操縱性應計利潤(NDA),最后通過式4計算實施MBO的上市公司在管理層收購當年及前后各2年的操控性應計利潤(DA)。
(二)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本文的研究對象為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自2000年至2007年期間實施管理層收購的上市公司。本文主要研究上市公司管理層在實施MBO前后是否對上市公司進行盈余管理行為,因此,樣本選取遵循如下原則:
(1)本文所研究的管理層收購是指實施收購后,管理層對上市公司具有實際的控制權,或能夠對上市公司的生產運營產生重大影響,而帶有股權激勵性質的管理層持股的上市公司。
(2)本文以股權收購協議簽署的時間作為實證研究中管理層收購的時間。上市公司轉讓價格已經確定,并且轉讓價款一般也已支付,管理層實際上已經獲得了對上市公司的控制權,并且獲得政府批準,因此,本文以股權轉讓協議的簽署日作為管理層實施收購的時間。
(3)本文所研究的管理層收購剔除由于上市公司原大股東減持使管理層自動成為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東或實際控制人。管理層沒有足夠的壓力或動力在管理層收購前實施“向下”的盈余管理,或在管理層收購后實施“向上”的盈余管理,有可能會影響研究的整體效果。(4)上市公司必須在MBO實施前2年上市交易,并且在MBO實施后2年內控制權沒有發生變化;管理層收購完成當年及前、后2年的財務數據必須完整,必須是2008年以前進行MBO的上市公司。不考慮2ooo~之前實施管理層收購的上市公司。因此選取了實施管理層收購的34家樣本公司,見表(1)。表(2)顯示了實施MBO的上市公司年度及行業分布。可以看出,樣本公司的行業分布涉及13個行業,以傳統行業為主,并且主要集中在制造業。樣本公司實施管理層收購的年度主要集中在2002年和2004年,這是由于在2003年財政部一度暫停對國有上市公司實施管理層進行審批,因此,導致2003年實施管理層收購的數量較少。本文選取配對樣本應同時滿足以下條件:與樣本公司的所屬行業相同或相近;與樣本公司的資產規模在實施MBO的前一年較為接近;配對樣本公司在同一時期沒有發生其它重大事項。本文數據來源為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中國上市公司資訊網(cnlist.eom)和國泰安數據庫(CSMAR數據庫)。
實證檢驗
(一)描述性統計樣本公司描述性統計如表(3)所示(表略)。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在實施MBO前后,公司的資產和凈資產規模呈現同步增長的態勢,但資產總額的增長幅度更為迅速;營業收入的增長趨勢沒有發生變化,現金流也一直保持與營業收入同步增長的趨勢,但增長的幅度要小于營業收入。而營業利潤和凈利潤卻呈現出先揚后抑的趨勢,但均顯著為正,這既可能是管理層在實施MBO前為降低收購成本增加費用或成本以減少公司的盈利,也可能是由于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在取得公司控制權后通過關聯交易轉移上市公司的利潤。因此,僅從實施MBO的上市公司5年的相關財務數據上無法判斷上市公司在實施MBO前后是否進行盈余管理。
(二)回歸分析樣本公司財務狀況差異性分析如表(4)所示(表略)。可以發現,上市公司的資產規模、總資產報酬率、營業利潤率、全年實現的收入和利潤均無顯著區別(T檢驗和Z檢驗均不顯著),這說明樣本公司和配對公司的規模和經營情況比較接近,無顯著差異,可以用配對公司比較好的控制規模、行業等對盈余管理行為分析的影響。進一步地,如表(5)所示(表略),通過研究發現,實施MBO的上市公司在管理層收購的前一年(T_1)和當年(T)的操縱性應計利潤的均值和中位數均為負,并在5%的顯著水平下顯著;在管理層收購前的第2年(T_2),操縱性應計利潤的均值和中位數均為正,但在5%的顯著水平下不顯著;在管理層收購后兩年內(T+I,T+2),操縱性應計利潤的均值和中位數均為正,并在5%的顯著水平下顯著。
【關鍵詞】 資本結構; 成長性; 投資不足
一、引言
成長性是企業努力追求的目標,是企業利益相關者共同關心的重要問題。有關資本結構與成長性之間的關系近年來成為熱點。面對成長機會,怎樣的負債水平能夠使企業更好地發展?盡管有關文獻展開大量討論,卻未能達成一致。本文通過研究不同成長性及不同自由現金流量的企業,來闡述負債水平與企業成長性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
二、文獻回顧與假設提出
(一)文獻回顧
現代資本結構理論以MM理論為基礎,隨后發展了權衡理論、順序偏好和市場擇時理論。其中發展了的權衡理論認為企業存在最優的資本結構,該資本結構是企業稅收優惠、破產成本及成本等之間的權衡。成本由Jensen,Meckling(1976)提出,成本理論認為在企業的成長過程中,存在股權成本與債務成本,股權成本是由于企業管理者和股東的目標不一致產生的。Jensen(1986)認為當企業存在過多的現金流量和較少成長機會時,由于管理者與股東的目標不一致,前者有擴張企業規模的動力,在此情況下將會產生過度投資問題,此時過度投資問題可以通過發行債券來緩解,引入負債可以起到監督和控制作用,這便是負債的相機治理作用。債務成本則是由于股東和債權人的目標不一致而產生的,Myers(1977)認為負債能引起投資不足,因為投資給債權人帶來了收益,而股東要承擔全部風險;同時企業擁有過高的負債比率時,股東將有強烈動機投資于高風險項目,發生資產替代行為,侵占債權人財產。成本的存在使得權衡理論進一步發展,同時也使得面對不同成長機會的企業,去尋找適合的資本結構來降低企業的成本,實現企業價值的最大化。
有關負債水平與企業成長性的關系,學者也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Langberg(2008)證明權益融資有利于促進企業成長,而債務融資會降低企業未來的成長機會。Muller(2009)以總資產增長率衡量企業成長性,表明財務杠桿對企業的成長性有顯著的負向影響。Huang和Song(2006)以銷售收入增長率衡量企業成長性,對我國主板上市企業進行了研究,得出成長性與資產負債率顯著正相關。Larry lang(1996)實證說明杠桿作用和企業增長間的負相關性對于具有低的Q值的企業成立,然而對于高Q值的企業來說并不成立。楊瑩(2009)以ROE劃分公司經營業績,當企業經營業績好時,財務杠桿與企業的成長性正相關,經營業績差時負相關。以上文獻說明,關于資本結構與成長性之間的關系尚未達成一致,有待更深入的研究,這也正是本文的意義所在。
(二)假設提出
當企業擁有較多成長機會時,企業將會選擇較低的負債率,成長機會是由一系列NPV>0的項目構成,當企業擁有較多這種項目時,為了避免債權人過多地分享收益同時又不承擔風險,高成長性企業將會選擇較低的負債率,基于此提出假設一:在高成長性企業中,成長性與負債水平負相關,即成長性越高的企業,傾向于選擇越低的負債水平。
而對于擁有較多自由現金流量的低成長性企業,由于存在較少的成長機會,可能出現上文所分析的管理者過度投資現象,因此認為此時企業可能會引入負債發揮其相機治理的作用,基于此提出假設二:擁有較多自由現金流量的低成長性企業,成長性與負債水平負相關,即成長性水平越低,負債水平越高。
上述兩種假設中,假設一擬證明投資不足現象,假設二則證明過度投資現象的負債治理功能。
三、研究設計:樣本、變量與模型
(一)樣本
本文選取滬深兩市主板制造業2006—2010年的數據,剔除數據不全、異常值及被ST的得到3 523個樣本。將樣本按照成長性進行分類,取成長性較高的前800名樣本作為高成長性樣本,后800名作為低成長性樣本,再從低成長性樣本中選取自由現金流量較高的前200名作為第三組樣本分析,以期完成樣本的對比及分類。本文數據均來自于國泰安CSMAR研究數據庫,計算分析利用SPSS18.0完成。
(二)論文模型
(三)變量設置
1.自變量的選取
對于成長性的描述通常采用兩類指標:(1)企業的實際增長率指標,如銷售收入增長率、總資產增長率、凈資產增長率、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增長率等。(2)資產市值賬面比、股東權益市值賬面比、盈余市價比、資本性支出占資產的比值、R&D占資產的比值、R&D占銷售收入比值等。Adam和Goyal(2007)進行的實證比較結果表明,資產市值賬面價值比為最可靠的企業成長性指標,盡管國內學者有將(1)類或(2)類指標進行組合,但并不能充分證明其優于資產市值賬面價值比,因此本文采用資產市值賬面價值來衡量企業的成長性。
2.控制變量選取的原因
DeAngelo 和Masulis(1980)認為無負債稅盾是債務的替代,無負債稅盾越高,公司越傾向于采用較少的財務杠桿,因此,認為無負債稅盾與企業的財務杠桿成反比。
有形資產作為債務的擔保,有形資產的比例越高,則企業所能使用的財務杠桿比例越高。
盈利能力采用ROE指標,根據Myers和Majluf的融資優序理論,盈利能力與杠桿之間的關系呈負相關,認為企業融資一般會遵循內源融資、債務融資、權益融資這樣的先后順序,因此盈利能力與杠桿比率成反比,但是基于稅收的模型認為,盈利能力較強的企業應更多地采用負債融資,以此來避開企業所得稅。
Frank和Goyal(2007)認為規模大的企業能承受更高的杠桿,這是因為規模更大的公司信息不對稱以及逆向選擇的可能性越小,這使他們更容易進入債券市場。
具體的變量說明見表1。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如表2)
(二)樣本的回歸結果
回歸結果表明對于高成長性企業樣本組,負債水平與企業的成長性在1%的水平下顯著負相關,即高成長性企業將會選擇較低的負債水平以減少債權人對收益的分享,因此假設一成立,驗證了投資不足理論。而低成長性樣本組的回歸結果表明,成長性和負債水平不相關,這一結論也從側面反映出高成長性樣本組結論的可靠性(如表3)。
而在低成長性、高自由現金流量的樣本組中,成長性與負債水平依然無相關性。說明具有較多自由現金流量的低成長性企業,通過提高負債來進行相機治理的假設二不成立,未能證明負債能有限減少過度投資的假設。而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國上市公司的主要債權人是商業銀行,而我國的商業銀行對上市公司的治理力度很弱,并不能有效地發揮治理作用。
而在其他影響負債水平的控制變量中:ROE與負債水平顯著正相關,證實了擇時理論,與理論預期一致;無負債稅盾與負債水平顯著負相關,證實了理論預期;而有形資產及公司規模與杠桿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這也與理論預期相符合。
五、研究結論與展望
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對于高成長性企業,負債水平與成長性顯著負相關,說明成本導致的投資不足理論顯著成立,同時說明企業在進行負債水平選擇時,將會根據企業的成長性進行適當的調整,這一結果豐富了權衡理論。
另一方面對于現金流量充足的低成長性企業,由于杠桿與成長性之間的關系不顯著,因此過度投資理論未能得到充分證實。債權人的審查監督機制未能得到充分發揮,作為債權人中的主要力量——銀行的監督治理作用也有待進一步加強,其中主要原因是法律對債權人的保護力度不夠,如《公司法》沒有大債權人派董事的規定等,貸款的軟約束問題不可避免。因此加強債權人的監督作用需得到法律的支持,這也是未來中國金融市場改革時需要注意的地方。
【參考文獻】
[1] Jensen,Michael C.,and William H.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and capital structure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305-360.
[2] Myers,Stewart C.,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borrowing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7(5):147-175.
[3] Jensen Michael C. Agency cost of free cash flow,corporate finance and takeovers[J].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1986(76):323-379.
[4] Langberg N.Optimal Financing for Growth Firms[J].Journal of Finance,1995(50):1421-1460.
[5] Muller E.Benefits of Control,Capital Structure and Company Growth[R].ftp//ftp.zew.de/pub/zew-docs/dp/dp0555.pdf.2009.
[6] Huang G.H.,Song M.F.The Determinants of Capital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6(17):14-36.
[7] Lang L,Ofek E,Stulz RM.Leverage,investment and firm growth[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6(40):3-29.
[8] 楊瑩.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對成長性影響的實證研究[J].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9] Adam T.,Goyal V.K The Investment Opportunity Set and Its Proxy Variables[R].Working Paper Series,SSRN-id1271056,2007.
[10] DeAngelo,H.,R.Masulis.Optimal Capital Structure under Corporate and Personal Taxat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0(8):3-29.
[11] Johnson,S.A.Debt Maturity and the Effects of Growth opportunities and Liquidity Risk on Leverage[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3(16):209-236.
[12] Matthew T.Billett,Tao-Hsien Dolly King,and David C.Mauer.Growth opportunities and choice of leverage,debt maturity,and covenants[J].Journal of Finance,2007,62(2).
關鍵詞:入職收入 關系資源 關系強度 市場轉型
求職過程及其結果研究是社會學的重要議題之一。這是因為社會學者關心社會分化、分層和流動問題,而職業是綜合反映分化、分層和流動的標志性地位指標,求職過程及其結果則是研究人們如何獲得這一標志性地位的根本視角。本期一同刊發的張順、郭小弦一文是根據結構特征模型探討這一過程和結果,即假定求職者是一個獨立決策的理性經濟人,所以解釋變量是個體的人口特征、人力資本、政治資本和家庭背景等。與之不同,社會網絡模型假定求職者是一個嵌入關系中的理性社會人,基于此,本文從微觀的角度探討社會關系對求職過程及其結果的影響程度。而王文彬、趙延東的論文探討社會關系對自雇者及其創業過程的影響作用。事實上,求職的微觀過程不是孤立進行的,而是在勞動力市場的大環境中展開、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發生的。這些環境和背景,一言以蔽之,稱為宏觀經濟結構。對于中國宏觀經濟結構如何影響求職過程中關系的嵌入程度及其變遷這一問題的分析將基于多層次模型,由梁玉成在其論文中進行闡釋。
求職過程及其結果的重要衡量指標是入職收入。如果是初職收入,它標志著社會學所謂“自致地位”的初步狀況和水平,預示著向上流動的前景;如果是流動后的入職收入,則標志著人們通過流動而達到的新的社會經濟地位,以及進一步上升的空間。這兩種不同的狀態具有同一性,即入職收入排斥了“內部勞動力市場”的約束和影響,因為它是人們從“外部勞動力市場”獲得的地位結果,本文關注影響這一地位結果的關系效應的性質和程度。如果能從理論上把握關系引發的是信息效應還是人情效應,并用實際數據測量兩種不同效應的相對程度,就能對當前外部勞動力市場的關系嵌入程度形成一個清晰的判斷,從而確定政策調整的方向和科學研究的任務。本文依據2009年城市求職網調查數據,對上述問題予以理論和實證分析。
一、理論背景與研究假設
經濟學將工資收入視為勞動者生產能力的函數,而達到預期生產率的那些勞動者,將得到市場均衡工資(Javanovic,1979)。但問題在于,生產能力是勞動者的潛在素質,雇主沒有條件觀察求職者的這一綜合素質,很難測量它。一些西方學者認為,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網絡的作用尤為重要,即雇主通過個人關系網絡得到求職者能力的種種信息擇優錄取(Stigler,1961;Akerlof,1970;Granovetter,1981)。理性主義導向的勞動力市場中,社會網絡提供的信息越精確,非重復性越強,則信息量越大、質量越高,雇主對求職者的評價越接近實際,所提供的入職收入也就越高(Granovetter,1973)。這就是入職收入的信息資源效應。
信息資源很難測量。以往研究受格蘭諾維特的影響,使用關系強度作為替代變量,其“弱關系”假設指出,越是交往不頻繁、關系不密切的弱關系,交往者之間的地位特征差異越大,相互傳遞的信息的重復性越小,信息量越大、質越高,所以使用弱關系找到工作的人,入職收入較高。林南(Lin,1982)發展了格蘭諾維特的理論,認為通過弱關系更可能聯系到地位較高的人,從而獲得更加優質的崗位信息。在Podolny(1993;1994)看來,能聯系到地位高的關系人則間接表明了求職者本人的才能不低,因此是一種信號機制,向雇主傳遞了關于求職者生產能力的信息。由此得到:
假設l:由于信息優勢,使用弱關系的求職者比其他求職者獲得較高的人職收入。
弱關系所預示的信息機制并非唯一的影響因素。交往頻繁、關系密切、相互熟悉的“強關系”預示著人情機制,同樣影響著個人的入職收入水平(Prendergast&Topel,1996)。當雇主接受朋友或同事的推薦時,不能完全排斥人情的影響,如果推薦人的地位高、權勢大、財富多,這種人情機制將變得十分明顯,雇主為此對被推薦人產生人情偏好(Rees,1966)。在這種情境下,雇主受制于關系,即社會學所謂的關系網絡的“嵌入性”,從而不可能完全理性地進行勞動力選擇(Granovetter,1985)。關系網絡的嵌入性越強,雇主就越有義務感去照顧被介紹來的求職者,比如,中國職業分配中的關系作用(Bian,1997)。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人情網絡不公正地獲得稀缺資源,事實上排斥了其他人參與競爭,這被稱作“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的負面效應”(Portes,1998)。如果上述過程影響了求職者的人職收入,我們將之概括為人情資源效應。
如果信息資源尚且難測,那么人情資源的測量則是難上加難。因為人情交換是背后交易,調查手段有限。研究發現,人情資源往往嵌入強關系之中。例如在美國,由于親朋好友向雇主施加了重要影響,求職者才能保證一個較高的入職收入,無論是學校畢業后的初職工資(Rosenbaum,et al.,1999),還是流動之后的工資水平(Coverdill,1998)。人情在日常生活中也存在許多例證,在美國,求職者經常訴求于他人“打招呼”(Corcoran,et al.,1980);而在中國社會中,強烈的關系主義文化背景的特點之一便是人情交換(Hwang,1987;King,1994;Yang,1994;Yan,1996)。在此背景下,強關系在職業流動中被頻繁使用,且富有成效(Bian,1997;Bian&Ang,1997)。因此得到:
假設2:由于人情優勢,使用強關系的求職者比其他求職者獲得較高的入職收入。
用關系強度代替關系資源曾推動了經驗研究,但也引起重大質疑,即關系強度不等于關系資源,替代變量既沒有提供穩定的實證結果(Bridges&Villemez,1986;Graaf&Flap,1988;Marsden&Hurlbert,1988),也不能通過嚴格的數據檢驗(Montgomery,1992)。最新的研究發現,關系強度對入職地位和入職收入的因果效應在美國數據中并不存在(Mouw,2003)。這一結論向研究者提出了挑戰:必須測量關系資源,而不能繞開它。邊燕杰和張文宏(2001)提出了這個問題,并用中國數據做了初步探索;邊燕杰和黃先碧(Bian&Huang,2009)則又做了進一步的分析。根據這些前期成果得到:
假設3:使用弱關系的求職者更可能動員關系網絡中的信息資源;而使用強關系更可能動員關系網絡中的人情資源。
假設4:從關系網絡動員了信息資源或者人情資源的求職者,比其他求職者獲得更高的人職收入。
信息資源和人情資源的相對效應如何呢?從市場化動態過程的角度看,社會網絡的收入效應是下降、持續還是上升,這涉及如何從理論上把握中國市場化動態過程的性質和特征。如果市場化機制的確立和完善過程是效率理性上升的過程,那么代表效率理性的人力資本將升值,而代表非效率理性的政治權力資本將貶值,即“市場轉型論”的核心假設(Nee,1989)。根據市場轉型輪,有學者進一步假設,社會網絡關系也是代表非效率理性的,市場化的發展越縱深,社會網絡關系也將貶值,即“關系下降論假設”(Guthrie,1998)。
與此相反的觀點認為,市場化機制的確立和完善過程中,由于政治體制穩定和“抓大放小”政策實施之后國有單位持續強勢,政治權力的作用將持續,甚至有條件地加強,這就是市場轉型研究中的“權力持續假設”(Bian&Logan,1996)。在權力持續的社會分層體系中,可以想象社會網絡關系作用的持續,因為權力運作往往增加了人為的成分,通過強關系尋找實權人物而得到人情回報的空間增大了。為此,在“體制洞”遍布轉型經濟的條件下,社會網絡關系對職業地位和收入獲得的效應不一定減少,很有可能增加(Bian,2002)。
本文采納邊燕杰等(Bian,2007;Bian&Zhang,2012)的觀點后認為,隨著市場競爭程度的提高和體制不確定性程度的提高,社會網絡的收入效應當增加。這是因為市場競爭越激烈,越要求行動者具有相對比較優勢,而體制的不確定性越高、規則模糊、權力運作不透明、交叉制度的兼容性低、社會網絡關系的作用越大,就越會提高行動者的比較優勢。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雖然市場競爭程度不會消減,但是體制不確定性將逐步下降,特別在世貿組織影響力度較大的區域和部門,這種趨勢比較明顯,為此,社會網絡的收入效應也隨之下降。因此得出:
假設5: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網絡中的信息資源和人情資源對入職收入的效應隨著市場化的深入逐年加強,但在進入世貿組織之后開始受到制約。
二、變量設計和描述
八城市調查的抽樣工作統一完成l,基于全國數據抽樣框,在各市隨機抽取城區居民委員會,每個城市作為單獨總體,抽取足夠的代表性樣本,各市初定為1 000戶,根據居委會抽樣的具體情況留出5%的調整余地。由于長春、濟南和廈門的城區相對較小,調查戶減至700個左右。為了滿足多層次分析所需要的條件,每個城市抽取足夠的社區樣本,每個社區抽取20戶,每戶隨機抽取一位具有非農、有收入工作經歷的成年人作為被訪人。調查前,我們對各市的外來務工人口做了深入研究,估計其規模,抽樣時按照估計的比例在選中的居委會抽取常住人口戶和外來人口戶。調查采取人戶面訪形式,按統一問卷進行,在2009年夏、秋兩季完成,復查率為10%。八城市調查最終收集有效問卷7 102份,問卷回答率60%。
八城市調查數據中,有6 307個被訪者曾有非農受雇工作經歷,構成本文的分析樣本(雇主和自雇不在其列),分析樣本的相關變量和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這里重點分析其中的四個關鍵變量。
入職收入是因變量,即被訪者獲得最近一份工作時的實際入職收入,平均月收入接近千元,標準差超過1 500元,入職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很大。由于該變量是右偏分布,所以取對數后進入分析模型。
關系強度是自變量,指被訪者獲得最近一份工作時是否使用了關系,如果是,與關系人的熟悉程度“熟極了”、“很熟”、“較熟”視為“強關系”,占29.9%;“不熟”、“不認識”(間接關系)視為“弱關系”,占29.4%;未使用關系占40.6%。
關系資源是重點自變量,指關系人提供的求職幫助屬于信息資源性質還是人情資源性質。根據深度訪談和前期研究經驗(邊燕杰、張文宏,2001;Bian&Huang,2009),研究區別兩種關系資源的性質,其關鍵是看關系人是否與雇主發生接觸,從而對其施加影響,獲取人情偏好。為此,我們將提供就業信息、介紹招工情況、提出申請建議和協助整理申請材料等視為“信息資源”;而將幫助報名、遞交申請、實名推薦、打招呼、安排面談、陪同造訪、承諾雇主要求和直接提供工作等視為“人情資源”。調查發現,有的求職者從關系人同時獲得不同性質的資源,還有的求職者不愿意說明所獲資源的性質,為此,產生了四種關系資源使用形態:信息資源(14.9%)、人情資源(9.2%)、信息和人情混合資源(23.9%)、關系資源不明(11.4%),未使用關系的占40.6%。
入職年代是自變量,旨在厘清關系的作用是否隨著改革的進程而發生變化,包括四個經濟體制時代:(1)改革前(1956-1979)的再分配經濟時代(25.3%),(2)改革初期(1980-1992)的雙軌制時代(22.2%),(3)改革中期(1993—2001)的經濟快速轉型時代(14.4%),(4)加入世貿組織后(2002年及以后)的全面市場化時代(37.5%)。
除了上述核心變量,數據分析還涉及被訪者的性別、年齡、戶口、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工作單位性質和所在城市,均視為控制變量。其中,單位部門的缺失值較多,占樣本的2.6%(見表1)。
三、假設檢驗
假設檢驗分三步進行。第一,檢驗弱關系是否更多地產生信息資源,強關系是否更多地產生人情資源(假設3);第二,檢驗關系強度對入職收入影響程度的假設(假設1和假設2),同時看關系強度的收入效應是否隨著改革時代而發生顯著變化;第三,檢驗關系資源對人職收入影響程度的假設(假設4),同時檢驗關系資源的收入效應是否隨改革時代而發生顯著變化(假設5)。
(一)強關系和弱關系帶來不同性質的資源
表2中的模型1表明,如果使用弱關系獲得信息資源的幾率為1(參照項,下同),那么,使用強關系獲取信息資源的幾率是O.470,大約降低了一半;模型2同樣以弱關系使用者為參照,其獲取人情資源的幾率為1,強關系使用者獲取人情資源的幾率為2.896,幾乎增加2倍;模型3進一步證明強關系的相對優勢:如果弱關系使用者獲取混合資源的幾率為1,強關系使用者獲取混合資源的幾率是3.061,差別超過2倍。這些結果證明假設3成立。這也說明,以往用關系強度代替關系資源的經驗研究是有事實根據的,但前者不能替代后者,因為強關系對信息和人情混合資源的動員作用也具有相對優勢。獲取什么性質的關系資源不受個人特征影響,不過,教育程度越高,獲取混合資源的幾率越大。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深入,單純使用人情資源的求職者變得越來越少。
(二)關系強度影響入職收入
表3第一部分結果顯示,利用關系而成功求職的比例從再分配時代的27.2%飆升到改革后期的81.6%,外部勞動力市場是一個不斷嵌入社會關系的市場。第二部分總樣本分析顯示,當控制入職時代和其他變量的情況下,相對于沒有使用關系的求職者來說,使用弱關系的入職收入高出12.2%(e0.115-1),使用強關系的求職者收入高出22.4%(e0.202-1),支持假設1和假設2。強弱關系回歸系數的差異,經T檢驗證實是統計顯著的,強關系的收入效應高于弱關系的收入效應10.2%(22.4%-12.2%)。舉例來說,如果沒有使用關系的入職月薪取均值1 000元,那么弱關系使用者的入職月薪是1 122元,強關系使用者的入職月薪是1 224元。這些人的個人能力和特征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關系使用導致了人職收入相當大的差異。
隨著改革年代的推進,這些差異發生變化了嗎?表3第二部分的分年代樣本的分析回答了這個問題。對于弱關系效應:改革前和改革初,弱關系的收入效應是正向的,但是統計不顯著,視為零,沒有效應;改革中期和后期開始發揮效應,但是比較小。對于強關系效應:改革前,強關系的收入效應比較大,而且統計顯著;改革初期,強關系的收入效應增加,統計顯著;此后,強關系的收入效應保持統計顯著水平,但是效應規模減少,低于改革前的水平。這個結果表明,深化改革之后,特別是進人世貿組織之后,勞動力市場對強關系的收入效應產生了很大的抑制作用。
(三)關系資源影響入職收入
這是本文的核心問題,相關統計結果見表3第三部分。總樣本分析拋開了強弱關系,引入關系資源變量后發現,在控制入職時代和其他變量的情況下,相比沒有使用關系的求職者,使用信息資源求職者的平均入職收入高出25.1%(e0.224-1),使用人情資源求職者的入職收入高出22.4%(e0.218-1),而使用混合資源求職者的入職收入會高出21.7%(e0.242-1),使用關系但資源不明求職者的入職收入高出15.4%(e0.166-1)。這些結果表明:第一,信息和人情資源對入職收入都有提升作用;第二,關系資源不明的求職者,其中一部分人確實獲得了信息或人情資源,另一部份人的關系作用不大,因為這組人的收入效應系數低于其他三組,但是高于沒有使用關系的求職者。總之,模型1的數據結果支持了假設4。
關系資源效應發生跨時代的變化嗎?表3中,信息資源效應在四個時期的系數都是統計顯著的,系數值從改革前的0.190提高到改革初期的0.234,改革中期略減到0.221,改革后期銳減到0.112,低于改革前的水平。人情資源效應在前三個時期的系數值統計顯著的,即從改革前的0.168提高到改革初期的0.289,改革中期略減到0.232,改革后期銳減到0.035,統計不顯著,視為零。混合資源效應的趨勢與人情資源系數類似,改革前低,改革初期高,改革中期下降,改革后期繼續下降,四個時期的系數均為統計顯著。本文在模型分析中保留資源不明一組,目的是保護樣本的完整性,其系數不做解釋。這部分數據結果說明,一方面,市場導向的改革擴大了關系作用空間,提高了關系效應;另一方面,隨著市場改革的縱深,尤其在進入世貿組織后,關系資源效應、特別是人情資源效應受到很大抑制。這些結果支持假設5。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選擇人職收入作為分析重點,基于最新數據,系統驗證了強弱關系理論和關系資源效應的研究假設。分析表明,經濟改革前后,弱關系對人職收入均無顯著影響,直到改革中期,特別是進入世貿組織之后,弱關系才開始對收入產生提升作用。強關系的收入效應在改革前后一直很大,但是進入世貿組織之后,開始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總的趨勢是,改革前和改革初,強關系效應大于弱關系效應;改革中期和加入世貿組織之后,前者在減弱,后者在增強。
社會網絡研究者一直認為強弱關系對應的資源機制是信息和人情,本文用最新數據驗證了這一觀點。“八城市調查”測量了求職過程中實際動員的關系資源類型,本文分析發現,使用弱關系有更高的幾率動員信息資源,使用強關系有更高幾率動員人情資源,但強關系有更大優勢動員信息和人情的混合資源。這說明,在中國,關系強度和關系資源是統計相關的,但是不能互相替代,經驗研究必須直接測量關系資源,不然就無法回答Mouw(2003)對于社會網絡因果解釋無效的質疑。研究結果顯示,不論信息資源還是人情資源,都有利于入職收入的提升,與沒有使用關系的求職者相比,提升效應在16%-19%之間,人情效應大于信息效應。
人情和信息效應的差距是有條件的,依改革時代的推進而變化。再分配時代,信息和人情的收入效應是存在的,這些效應在改革初期和中期迅速加強,但進入世貿組織后人情效應受到抑制,與強關系效應受到抑制相似。本文認為,改革開放進程中,勞動力市場的競爭程度上升,與此同時體制的不確定性程度也在上升,“體制洞”充斥市場空間,使得社會關系網絡和社會關系資源活躍其間。但是隨著改革深化,特別是中國進入世貿組織之后,關系效應有所抑制,開始下降,特別是人情資源效應受到很大約束(Bian,2007;Bian&Zhang,2012)。這是宏觀環境對微觀關系機制的制約作用,分析證明需要借助宏觀一微觀多層次模型(參見本期梁玉成一文)。
土地流轉作為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點受到了廣泛的關注,但土地流轉能否顯著增加農民收入,達到改善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目的,現有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結論。本文在文獻回顧和總結的基礎上,依據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運用傾向值匹配(PSM)方法和基于回歸的夏普里值分解(Shapley Value)方法,從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兩個維度實證分析土地流轉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①參與土地流轉能夠顯著提高農戶家庭收入水平。土地流轉使轉入戶家庭人均總收入和農業收入顯著提高18.18%和72.46%,并且大規模轉入的農戶人均總收入的增加程度顯著高于小規模轉入農戶,說明土地流轉存在規模效應。土地流轉對轉出戶的收入水平沒有顯著影響,可能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土地流轉市場發育不完善,沒有顯化租金;另一方面勞動力轉移先于土地流轉,使土地流轉對農戶家庭勞動力的釋放作用不顯著。②土地流轉對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貢獻度為4.19%,排名第五,表明土地流轉不是造成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人力資本和村莊特征對農村內部收入差距影響較大。根據研究結論提出三點政策建議:第一,通過完善農地流轉市場,穩定土地租金水平,使轉出戶獲得合理的租金收入;第二,促進農地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轉入戶農業經營收入,縮小農戶與非農經營戶之間的收入差距;第三,提高農戶就業競爭力,促進勞動力轉移,增加轉出戶非農務工收入。
關鍵詞土地流轉;農民收入;收入不平等;傾向值匹配;夏普里值
中圖分類號F303.3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7)05-0111-10DOI:10.12062/cpre.20170338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實施,我國農村居民的收入整體提高。但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改革效應逐漸下降,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并呈現不穩定和非持續性態勢,與之相伴的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農村居民的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22上升到2011年的0.39,30年間增長超過了50%。高度平均的土地分配以及隨人口變動頻繁進行的行政性調整嚴重影響了地權穩定性和耕作效率,阻礙農地適度規模化經營和農業現代化發展,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收入分配持續惡化。近年來,土地流轉作為一種新的土地資源配置方式得到快速推廣運用,也被政府部門和較多學者寄予厚望[1- 2]:希望通過土地流轉促進農地集中和規模化經營,進而促進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緩解收入差距。然而,現行政策體系下的土地流轉能否顯著增加農民收入,達到改善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目的,現有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結論[3-6]。本文利用2010年中國家庭追蹤調說氖據,以農戶家庭收入水平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參與土地流轉與農民增收、農民收入差距間的關系,驗證土地流轉對農戶家庭收入的影響,為土地流轉的收入效應研究提供新的證據,并將對完善和優化土地流轉政策提供實證支撐。
1文獻回顧
土地流轉市場的發展和影響引起了眾多學者的關注,其中對土地流轉與土地利用效率、農戶收入及農戶間收入差距變動成為研究的重點之一。學者們對土地流轉的效率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土地市場在優化生產要素配置[2,7]、提高農戶福利水平[8]方面的影響等方面,認為土地自由流轉促使土地資源從生產效率低的農戶手中流轉給生產效率高的農戶,產生邊際產出拉平效應[9],提升了總的資源配置效率。〖JP+1〗Deininger & Jin[7]根據1997―1999年中國最窮的三個省的1 001個農戶樣本數據,運用OLS估計發現,土地市場化流轉能更好地促進土地生產績效的提高。從理論上來說,土地流轉作為土地行政調整的替代機制,只要是在依法自愿基礎上進行,就能夠優化土地資源的配置效率,提高農業生產效率[10],提高農戶福利水平。
土地流轉與農戶收入之間的關系也受到廣泛關注,研究結論也較為一致。Zhang利用浙江的調研數據估算出農戶土地面積增加1%可以增加0.79%的家庭農業收入[11]。Jin & Deininger[12]對2001―2004年中國9個農業大省的8 000個農戶數據進行OLS估計,分析了土地流轉對農戶人均收入分布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不論是轉入還是轉出土地,農戶收入都有所增加。李慶海等[13]根據農業部農村固定觀察點2003―2009年10個省份817個農戶數據,利用Biprobit模型估計土地流轉的福利影響,研究發現土地流轉能夠提高農戶福利水平。此外,薛鳳蕊等[14]、李中[15]通^DID模型分別研究對比了鄂爾多斯市和湖南省邵陽市參與土地流轉農戶的收入變化,結果表明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收入水平明顯提高。這些研究說明,隨著土地流轉、農地經營規模擴大,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從而使土地流轉的收入效應得到發揮。但Khan的研究發現農戶土地經營面積的增加對農戶家庭收入的影響并不顯著,每增加一畝土地僅能為中國農戶家庭農業收入增收1.18元[16]。曹瑞芬等[5]利用湖北省313戶農戶調查數據,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估計土地流轉的收入效應,發現土地流轉能夠顯著提高轉入戶的收入水平,但對轉出戶家庭收入沒有顯著影響。
另一些學者關注了土地流轉能否改善農戶的收入分配公平,但研究結論之間存在較大不一致。Deininger & Jin認為,若土地市場是有效率的,年邁的或已經轉移到非農部門的農民能夠流轉土地獲得財產性收入,持續種田的農戶能夠擴大土地規模提高經營性收入,而這個收入與從事非農生產的農戶收入水平相當,那土地流轉將會緩解收入不平等[7]。與此結論相似的是Zhang[11]和韓菡等[6]等分別根據各自的農戶調查數據分析認為,土地流轉有利于改善農戶間收入不平等。但學者邢鸝等[17]和朱建軍等[3]等基于農戶調研的數據研究表明土地流轉加劇了農戶收入分配不平等。
〖JP+1〗由于不同研究中的農戶所處的區域社會經濟條件、土地流轉市場發育程度和政府干預手段的不一致,客觀上都會造成土地流轉對農戶收入影響的不一致。其次,農戶是否參與土地流轉存在自選擇問題,這導致土地流轉決策會受到一些無法觀測的變量影響。現有的大多數測算土地流轉對農戶收入影響的研究沒有考慮到樣本農戶的自選擇問題,直接使用OLS估計方法易高估處理效應,也可能導致了研究結論的不一致。此外,在探討土地對農民收入差距的文獻中,大多研究僅將土地變量作為農戶的特征變量,較少文獻具體考察土地流轉作為關鍵變量對收入差距的影響,缺乏估計土地流轉對農民收入差距的貢獻度。
作為對已有文獻的補充,本文著重從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兩個維度分析土地流轉對農民收入的影響,運用樣本量較大和覆蓋范圍較廣的中國家庭追蹤調耍CFPS)數據,估計土地流轉的收入效應,驗證政府土地流轉政策是否存在偏誤,為政府進一步健全土地流轉制度提供實證支撐。與以往文獻不同,本文研究充分考慮到土地流轉的自選擇問題,首先,以反事實框架為分析依據,采用傾向值得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將參與土地流轉戶與未流轉戶進行匹配,準確估計土地流轉對收入水平的影響;其次,運用基于回歸的夏普里值(Shapley Value)分解方法,設定農戶收入決定方程,估計土地流轉對農村收入差距的貢獻度。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新意,在研究內容上也更為完整。
2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2.1模型設定
(1)傾向值得分匹配。傾向得分匹配法是一種非參數法,該方法通過構建一個反事實框架,在解決選擇性偏差問題方面具有較強的可行性和科學性[4,18-20]。由于是否參與土地流轉是農戶自己決定的,存在樣本選擇偏差,若忽略該問題直接對方程進行估計,則會造成估計結果有偏。傾向得分匹配法能夠通過匹配再抽樣的方法使觀測數據盡可能接近隨機實驗數據,在最大程度上減少觀測數據的偏差,因此傾向得分匹配法可以更準確地估計土地流轉的凈收入效應。
本文假定農戶家庭收入水平是參與土地流轉以及協變量(控制變量)的函數:
根據Rosenbaum & Rubin定義的反事實分析框架,定義農戶i參與土地流轉的處理效應,即平均處理效應(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
其中,Y1i表示農戶i在參與土地流轉時的收入水平,Y0i表示農戶i不參與土地流轉的收入水平,ATT表示流轉戶參與與不參與流轉條件下的收入差值,即土地流轉對農戶收入水平的凈效應。然而如果農戶i參與土地流轉,則只可觀測到E(Y1|D=1),無法觀測到E(Y0|D=1),可以利用傾向得分匹配法構造E(Y0|D=1)的代替指標。
傾向得分匹配法的基本思路是:在未流轉農戶樣本(控制組)中找到某個樣本j,使樣本與流轉農戶樣本中(處理組)樣本除參與土地流轉情況不同外,其他特征盡可能相似,即兩個樣本具有可比性,因此可將兩個樣本的收入水平近似認為是同一個體的兩次不同實驗(參與和不參與土地流轉)結果,收入水平的差值則為土地流轉的凈收入效應。具體估計過程主要包括四步:第一,將農戶依照參與土地流轉與否分為處理組(D=1)和控制組(D=0);第二,給定協變量Xi的條件下,估計每個樣本農戶選擇土地流轉的條件概率pi=p(Xi)=Prob(D=1|Xi),即傾向值得分;第三,找到控制組的某農戶j,使農戶j與處理組的某農戶i的可觀測變量取值盡可能相似,即Xi≈Xj。在理論上存在多種匹配方法,且匹配結果是漸進等價的,因此,本文選擇采用最近鄰匹配法。第四,根據匹配的樣本估計平均處理效應(ATT)。在使用傾向值得分匹配之前,要滿足兩個假定:①可忽略性假設。在控制了Xi后,農戶家庭收入水平將獨立于農戶是否參與土地流轉;②共同支撐假定。保證處理組農戶與控制組農戶的傾向得分取值范圍有相同的部分。當滿足了以上兩個假定后,也就是說匹配后未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收入E(Y0|D=0)可近似代替參與土地流轉農戶不參與土地流轉的收入E(Y0|D=1)。
(2)基于回歸的夏普里值分解。為了能夠量化土地流轉對農村內部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貢獻,本文應用Shorrocks和Wan基于回歸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21]。該方法適用于任何收入決定函數和任何度量收入差距的指標,并且能夠很好地處理常數項和殘差項對收入差距的貢獻的問題。
首先,設定農戶收入決定方程,回歸方程具體形式如下:
其中,lnYi表示農戶家庭人均總收入的對數,Wi表示影響農戶家庭收入的自變量,是前文傾向值匹配的協變量Xi篩選后的變量,進行變量篩選主要是基于以下幾點原因:①造成農村收入差距的因素主要分為外部環境因素和家庭自身因素兩方面,主要有地理區位因素[22]、物質資本[23-24]、人力資本[25]、社會網絡資本[26]。前文傾向值匹配模型中自變量的選擇通常是用來篩選處理組和控制組的樣本,而收入決定方程不需要過多的控制變量;②由于使用的分解方法涉及許多輪的運算,每增加一個變量,程序的運算量將呈幾何級數增長,當變量超過10個時,由于運算量過大無法得到結果[26],因此,為了簡化計算,在分解時的收入方程中僅選擇關鍵的自變量。
其次,將收入差距的計算指標運用到該方程的兩端,從而得出各自變量對于收入差距指標的貢獻度[27]。由于收入決定方程使用的是半對數模型,在分解時需要改寫收入變量Yi的決定方程,即方程兩邊取指數,得到待分解的方程為:
在收入差距的形成過程中,一個因素對于收入差距的貢獻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①該因素與收入差距的相關系數,即該因素對于收入的偏效應,在給定該因素的分布下,系數越大,該因素對收入差距的貢獻越大;②該因素自身的分布狀況,在給定該因素對收入的相關系數不變的情況下,它的分布越不平均,那么該變量對于收入差距的貢獻也更大,反之亦然。極端地講,當一因素對收入的偏效應接近于0或者它的分布完全平等時,那么該因素對于收入差距的貢獻為零。
2.2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數據來自于中國家庭追蹤調耍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簡寫CFPS)。CFPS是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ISSS)實施的全國性、綜合性的社會跟蹤調查項目,全國基線調擻2010年開展,通過跟蹤收集個體、家庭、社區三個層次的數據,反映了中國家庭的人口特征、收支情況、農業生產、經濟活動以及非經濟福利等變化。調查對象為中國25個省/市/自治區(不含香港、澳門、臺灣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自治區、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海南省)中的家庭戶和樣本家庭戶中的所有家庭成員,其分層多階段抽樣設計使得樣本能夠代表大約95%的中國人口。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農村家庭,剔除遺漏關鍵信息以及存在嚴重異常值的農戶家庭,經過復核整理,最終獲得有效農戶樣本5 226戶,樣本涵蓋了24個省(直轄市),其中東部地區11個省(直轄市),中西部地區13個省(直轄市)。
3實證分析與結果
3.1基本描述統計
本文使用農戶家庭人均總收入、非農收入、農業生產純收入三個指標來表示農戶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結構,將農戶分為未流轉農戶、流轉農戶、轉入戶與轉出戶四類進行家庭收入水平比較。如表1所示,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家庭收入水平高于未流轉農戶,流轉戶家庭人均總收入、非農收入、農業生產純收入較未流轉戶分別高0.15萬元、0.06萬元、0.31萬元。轉入戶家庭人均總收入均值為0.74萬元,農業生產純收入1.08萬元。轉入戶從土地流轉中獲得較高的農業收入,也使得轉入戶的家庭收入水平
高于其他類型農戶。非轉入戶的非農收入是家庭收入的重要來源,轉出戶有更多的非農就業機會,其家庭人均總收入要高于未流轉戶。但參與流轉農戶與未參與農戶的初始條件不完全相同,簡單直接對比不同類型農戶的收入情況是不準確的,無法避免“選擇偏差”,所以本文通過模型分析對該結果進行驗證。
3.2變量選取
本文選取的被解釋變量為農戶家庭人均總收入、非農收入、農業生產純收入,為更好地反映土地流轉對農戶家庭收入水平的影響,對因變量進行對數處理。關鍵變量為農戶家庭是否進行土地流轉,0表示未流轉土地,1表示流轉土地。根據模型設定以及可忽略性假設的要求,盡可能多的控制那些對農戶流轉土地決策以及農戶家庭收入水平產生影響的變量,并且這些變量不受是否參與土地流轉的影響[28]。本文共選擇三類變量:家庭主事者特征,包括農戶家庭經營決策者的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等;家庭特征,包括經營土地的面積、家庭規模、勞動力結構、家庭資產等;村莊特征,包括村莊人口規模、人均耕地面積、村級經濟水平、地形地貌、地區虛擬變量等,統稱為協變量,具
體變量描述見表2。
3.3土地流轉對農戶收入水平的影響
研究關注的被解釋變量為農戶家庭收入水平,通過農戶家庭人均總收入、非農收入、農業生產純收入衡量。為保證匹配質量,對模型進行了平衡性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模型很好的平衡了處理組和控制組的數據,在匹配后并無明顯差異,通過平衡性檢驗。表3給出了全樣本農戶進行傾向值得分匹配的估計結果。對全樣本農戶進行傾向得分匹配前,參與土地流轉與未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家庭人均總收入對數分別為8.513和8.267,兩者之間的差異為0.246,運用最近鄰匹配方法將控制組與處理組進行匹配,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家庭人均總收入為8.513,而未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家庭人均總收入為8.351,這表明在考慮了土地流轉的樣本選擇偏差問題后,土地流轉對農戶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作用變小,兩者之間的差異為0.162,并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個差異為參與土地流轉的平均處理效應(ATT),表明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平均家庭人均總收入比未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高17.59%(exp(0.162)-1)。從不同收入類型來看,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家庭農業生產純收入比未流轉農戶高47.70%(exp(0.390)-1),但對非農收入的增加效應在統計意義上不顯著。
考察完全樣本,再將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家庭進一步細化為轉入和轉出土地的農戶家庭進行估計分析。不同農戶家庭在參與土地流轉后有不同收入增長路徑,轉入戶通過擴大生產規模、提高農地利用效率影響家庭收入水平,而工資水平、非農就業的競爭力和土地流轉的租金是影響轉出戶收入的主要因素。運用傾向值匹配估計這兩類家庭的收入效應是否一致,研究土地流轉對不同類型農戶的收入影響差異,估計結果見表4。
根據估計結果可知,土地轉入戶比未流轉戶的人均總收入平均提高了18.18%(exp(0.167)-1),并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從分項收入來看,土地轉入能夠使已參加土地流轉的農戶家庭農業生產純收入顯著增加約72.46%(exp(0.545)-1),對家庭非農收入的影響統計水平上不顯著。對轉出戶的分析結果表明,參與土地轉出后,農戶家庭人均總收入提高4.08%(exp(0.040)-1),非農收入增加28.02%(exp(0.247)-1),農業經營純收入減少10.52%(1-exp(0.010)),但在統計水平上未達到顯著。
通過對全樣本和不同農戶類型樣本的估計,從實證結果上證明了先前的理論研究結論[2-4,9-10,20]:土地流轉能夠顯著提高農戶的家庭收入水平。從不同類型農戶的估計結果來看,土地轉入能使農戶家庭人均總收入、農業經營純收入顯著提高。由于生產要素不可無限分割的特征,在狹小的土地規模下,勞動力、機械等主要生產要素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降低了這些要素的使用效率[29],因此,適度擴大土地經營規模獲取規模收益,可以達到增加經營者收入的目的。大量的實證經驗證明土地規模與糧食產出之間顯著相關,適度擴大土地規模能夠有效提高糧食產量[30-31]。農戶轉入土地后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研究表明土地轉入戶的邊際土地生產率明顯高于未流轉戶,土地流轉增加了土地配置的效率,通過適度擴大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實現農業規模化和現代化經營,使土地資源的效益得以更充分的發揮,提高農戶家庭經營收入。土地轉入對非農收入的影響不顯著,這是由于土地轉入與非農勞動力雇傭市場的關系并不顯著相關[2]。
對轉出戶的分析Y果表明,土地轉出雖然能夠增加農戶家庭收入水平,但影響并不顯著,可能的原因有兩點:一是盡管土地流轉市場發育進展很快,但仍有不少研究表明土地流轉市場并未發揮出全部潛力。Deininger & Jin的研究發現通過土地租賃市場的流轉總是伴隨著較高的交易成本[7],調查數據顯示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近一半的土地流轉是口頭的、周期性的、無償的[12,32],土地流轉中土地價值難以有效衡量,土地租金水平較低,這就導致在一定程度上,土地流轉對轉出戶家庭收入水平的影響不顯著。再有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在土地轉出前農村勞動力已進行初步轉移,土地轉出行為對農戶家庭非農勞動力的釋放作用不大。在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中,有大批曾經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村居民改變了生存方式,年輕且受教育程度好的勞動力已在外務工多年,因此,土地轉出對提高轉出戶家庭收入水平的影響效應不顯著。
前文已經證明土地流轉能夠顯著提高農戶家庭收入水平,但不同的流轉規模是否會造成不同的收入效應還需要進一步驗證。將轉入戶樣本按照轉入面積的中位數(3.95畝)劃分為大規模轉入戶樣本和小規模轉入戶樣本,分別進行傾向值得分匹配(由于樣本中土地轉出規模較小,土地轉出面積的中位數為2.15畝,未形成規模轉出效應,進行分組研究意義不大,故本文僅研究土地轉入規模分組)。對于大規模租入戶來說,參與土地流轉能夠顯著提高人均總收入21.17%(exp(0.192)-1),分項收入中,土地轉入會顯著減少非農收入55.12%(1-exp(0.439))、顯著增加農業經營純收入86.82%(exp(0.625)-1)。而小規模轉入戶參與土地流轉顯著提高人均總收入15.26%(exp(0.142)-1)、農業經營純收入31.00%(exp(0.270)-1),另外,土地轉入可提高小規模轉入戶家庭非農收入30.21%(exp(0.264)-1),但這部分效應在統計水平上未達到顯著。
估計結果表明,土地流轉對不同流轉規模農戶的收入效應影響存在差異。大規模轉入的農戶人均總收入的增加程度顯著高于小規模轉入農戶,差異主要來自于家庭農業經營純收入,大規模轉入戶農業經營純收入的增加程度是小規模轉入農戶的近3倍,這可能是因為土地轉入規模大的農戶更易達到規模經營,實現農業生產規模化和現代化,分攤生產的固定成本,得到更高的規模收益。而小規模轉入的農戶土地轉入規模小于3.95畝,經營規模較小,難以形成規模化生產,導致收入的增加程度較小。從家庭非農收入來看,大規模轉入戶的家庭非農收入顯著減少,而小規模農戶的不顯著增加,可能的原因是,小規模轉入戶的家庭多以兼業農民為主,家庭的收入來源不僅依靠農業收入,非農部門經營收入也是家庭收入的重要部分,而轉入小規模的土地對農戶家庭增收作用較小。
3.4土地流轉對農民收入差距的影響
土地流轉的收入效應除了對收入水平的影響,還包括對收入差距的影響。本文應用基于回歸的夏普里值方法計算土地流轉對農民收入不平等的貢獻度,并通過變量排序對其重要性做出判斷。
首先對農民收入決定方程進行估計,估計結果見表5。在方程(1)中去掉本文所關心的土地流轉變量,用來作為基準方程,在方程(2)中將土地流轉變量再加入進來。通過對比可以發現,兩個方程的回歸結果基本沒有太大變化,方程(1)中在1%和5%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的自變量在方程(2)中也在同樣的水平下顯著。對于本文關心的土地流轉變量,在方程(2)的估計結果中發現,在加入土地流轉變量后,方程中其他變量系數和顯著性都沒發生太大變化的前提下,使方程的R2提高,這說明在樣本家庭中,土地流轉對于收入決定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
從回歸結果來看,各因素對收入的影響方向與理論上的預期較為一致。土地流轉能夠顯著提高農戶收入。村莊特征中村莊經濟情況對農戶家庭人均總收入呈顯著正影響。家庭特征中,家庭規模越大,人均總收入越低,可能是由于收入水平相同的家庭,家庭規模大而撫養負擔更重,е氯司總收入降低。工資者比例變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城市化比率,估計結果表明工資者比例變量與人均總收入水平呈正向影響,說明城市化有利于提高農戶家庭收入水平,這也較符合當前非農工資性收入普遍高于農業經營收入的現狀。在人力資本中,家庭主事者的教育程度對家庭收入水平呈顯著正向影響,教育年限越長,積累的人力資本越多,家庭收入水平越高;而家庭主事者的年齡對家庭收入水平影響顯著為負,可能是由于年齡較大的家庭決策者雖然生產經驗較豐富,但觀念在適應新時代方面相對困難,導致部分家庭決策不能提高農戶家庭收入。資本是收入函數中的重要變量,人均農業投資對家庭收入水平影響顯著為正。實物資本用農戶家庭人均土地面積衡量,土地作為農戶家庭重要的資產,對家庭收入水平的影響顯著為正。
在分解之前,對模型進行解釋程度檢驗,計算1減去殘差作用的比率為51.9%〖HT6〗①〖HT9.5SS〗,表明收入方程中的自變量能夠很好地解釋收入差距,從而保證了本文分解結果的可靠性。其次,根據上述收入決定方程的估計結果,在此基礎上利用夏普里值的框架分解出各個解釋變量對于農民收入差距的影響程度。表6列示了分解后的結果,每個變量的貢獻度為該變量對基尼系數的貢獻,按該貢獻度對各影響因素進行排名。首先考察本文的重點關注的土地流轉變量。分解結果表明土地流轉變量對農戶家庭收入差距的貢獻度排在第五名,為4.19%,這個結果表明,土地流轉不是造成農戶收入差距的關鍵變量。可能的原因是,轉出戶家庭擁有的土地規模有限,參與土地流轉的面積更小,大約只有2畝,而轉入戶土地流轉規模也較小,樣本中位數為3.95畝,未能形成農地經營的規模效應,因此土地流轉對農戶家庭收入差距的影響不顯著。
家庭主事者的教育程度、年齡合并為人力資本變量,這個因素導致的收入不平等占總不平等近40%,排名第一,表明人力資本因素對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重要影響。
估計結果顯示教育的貢獻度為17.93%,這與Morduch J和 Sicular T對中國的研究結果相似[33]。結果證明教育不平等會顯著拉大農村家庭收入差距。
代表村莊特征的兩個變量加總對農戶家庭收入不平等的貢獻率排名第二,貢獻度為20.96%,這個結果與許慶等[24]、趙劍治等[26]的研究結果相似。表示村莊特征的“地區虛擬變量”不僅捕捉到地理差異,還反映出由地理差異造成的經濟條件、政策、市場整合程度等方面對農村收入差距的影響。
人均資本投入變量對農村收入不平等的貢獻度為17.96%,排名第三,與萬廣華等[22]的研究結果相似,他們運用夏普里值分解得到資本對農村內部收入不平等的貢
獻比重達16%―24%。隨著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農業部門的資本密集程度越來越高,資本分配不均對農戶家庭收入不平等的貢獻度也就較高。家庭特征對農戶收入差距貢獻度排名第四。家庭規模對農民收入不平等的貢獻度為12.62%,家庭人口越多,意味著負擔越重,人口負擔率越高,對農民收入不平等的貢獻度自然越大。
人均土地面積對農戶收入差距的貢獻度為3.47%,位列第五,說明農戶層面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資本而非土地等物質資本,與高夢滔等的研究較為相似[23]。可能的原因是土地在農村內部是均分化程度較高,不同農戶之間的差異較小,導致土地流轉中因人均土地面積對家庭收入差距的貢獻度不高。
4結論及政策啟示
本文基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利用傾向值匹配方法分析土地流轉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基于回歸分析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測算土地流轉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貢獻率,實證分析發現:①土地流轉存在收入效應,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比未流轉戶的人均總收入、農業收入顯著高17.59%、47.70%,但對非農收入的增加效應在統計意義上不顯著;②從不同類型農戶來看,土地流轉使轉入戶家庭人均總收入、農業收入顯著提高18.18%、72.46%,但土地流轉對轉出戶的收入水平]有顯著影響。從不同流轉規模角度分析,大規模轉入的農戶人均總收入的增加程度顯著高于小規模轉入農戶;③土地流轉對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貢獻度為4.19%,排名第五,表明土地流轉不是造成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人力資本和村莊特征對農村內部收入差距影響較大。
基于研究結論,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含義:
(1)完善農地流轉市場,穩定土地租金水平。土地流轉能夠顯著提高農戶家庭收入水平,說明促進土地流轉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一個功能良好、流轉價格合理的土地流轉市場,能夠滿足期望放棄土地使用權以更好地轉移到非農部門的農戶需求,同時也能滿足期望擴大生產規模繼續從事農業的農戶要求。因此,發展功能完善的土地流轉市場仍是現階段的土地流轉政策的主要目標,應積極建立和完善鎮、縣、市、省四級聯網的流轉交易信息公開平臺,使土地流轉的供求雙方能便利地獲得所需信息,促進土地流轉。同時通過交易信息的公開,也有利于通過市場機制形成土地流轉價格,從而形成為供求雙方都能接受的合理價格,既使得轉出方獲得合理土地租金收入,也使得轉入方有正常的經營收入,從總體上增加參與流轉的農戶收入。
(2)促進農地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轉入戶農業經營收入。轉入土地的農戶大多具有豐富的農業生產經驗或技能,土地流轉后能夠形成規模效應,有效提高勞動和土地生產效率,推動農戶家庭收入增加。應通過完善農村金融市場,提供信貸優惠政策,推動具有農業生產技能的農戶轉入土地;增加對種糧規模經營主體補貼,提高大戶種糧積極性;加強農田基礎設施建設,為農業規模化生產創造條件,增加農業規模經營收入,縮小農戶與非農經營戶之間的收入差距。
(3)提高農戶就業競爭力,促進農地轉出戶的勞動力轉移。轉讓土地經營權之后,農民在得到流轉租金的同時相應地減少了家庭農業經營收入。一般而言,土地租金收入會少于轉出戶家庭農業經營的減少額。此時,如果農戶外出務工不穩定或質量不高,非農收入也相對較低,最終會導致轉出戶家庭總收入水平下降。反之,則農戶家庭收入可能會增加。目前農村非農收入已經成為了農戶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單純的土地流轉租金對轉出戶家庭收入影響并不顯著。增加這類農戶家庭收入主要還是要靠提高其非農就業競爭力,增加其非農收入水平。因此,要通過針對性的職業培訓、就業推薦等政策來提高轉出戶家庭非農收入。年紀較大、不適合外出務工的農戶,一般具有相對豐富農業生產經驗,可由村社推薦至農業經營大戶或農業園區就業,成為農業勞動雇工;也可以由村社提供公益性崗位統一培訓,就地安置。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KIMURA S, OTSUKA K, SONOBE T, et al. Efficiency of land allocation through tenancy markets: evidence from China[J].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2011,59(3):485.
[2]HUANG J, GAO L, ROZELLE S. The effect of offfarm employment on the decisions of households to rent out and rent in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12,4(1):5-17.
[3]朱建軍, 胡繼連. 農地流轉對我國農民收入分配的影響研究――基于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數據[J].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5(3):75-83. [ZHU Jianjun, HU Jilian.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farmland transfer on farmers’ income distribution: based on CHARLS data[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5(3):75-83.]
[4]陳飛, 翟偉娟. 農戶行為視角下農地流轉誘因及其福利效應研究[J]. 經濟研究, 2015(10):163-177. [CHEN Fei, ZHAI Weijuan. Land transfer incentive and welfare effect research from perspective of farmers’ behavior[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5(10):163-177.]
[5]曹瑞芬, 張安錄. 中部地區農地流轉經濟效益分析――基于湖北省27個村313戶農戶的調查[J]. 中國土地科學, 2015(9):66-72. [CAO Ruifen, ZHANG Anlu. Analysis on economic benefits of farmland transfer in Central China: based on the survey of 313 peasant households of 27 villages in Hubei Province[J]. China land sciences, 2015(9):66-72.]
[6]韓菡, 鐘甫寧. 勞動力流出后“剩余土地”流向對于當地農民收入分配的影響[J]. 中國農村經濟, 2011(4):18-25. [HAN Han, ZHONG Funing.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labor force transfer and land transfer[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1(4):18-25.]
[7]DEININGER K, JIN S. The potential of land rental market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5,78(1):241-270.
[8]OTSUKA K, HAYAMI Y. Theories of share tenancy: a critical survey[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88,37(1):31-68.
[9]姚洋. 中農地制度:一個分析框架[J]. 中國社會科學, 2000(2):54-65. [YAO Yang. The system of farmland in China: an analytical framework[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0(2):54-65.]
[10]ZHANG Y, WANG X, GLAUBEN T, et al. The impact of land reallocation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a[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1,42(4):495-507.
[11]ZHANG Q F. Retreat from equality or advance towards effciency? land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Zhejiang[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8,195(1):535-557.
[12]JIN S, DEININGER K. Land rental market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productivity and equity impacts from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9,37(4):629-646.
[13]李慶海, 李銳, 王兆華. 農戶土地租賃行為及其福利效果[J]. 經濟學(季刊), 2012(1):269-288. [LI Qinghai, LI Rui, WANG Zhaohua. The land rental market and its welfare effects[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12(1):269-288.]
[14]薛鳳蕊, 喬光華, 蘇日娜. 土地流轉對農民收益的效果評價――基于DID模型分析[J]. 中國農村觀察, 2011(2):36-42.[XUE Fengrui, QIAO Guanghua, SU Rina. The effect of land transfer for farmers’ income:based on DID Model[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1(2):36-42.]
[15]李中. 農村土地流轉與農民收入――基于湖南邵陽市跟蹤調研數據的研究[J]. 經濟地理, 2013,33(5):144-149.[ LI Zhong. Transfer of rural land and farmers’ income:based on the tracking research data in Shaoyang, Hunan[J]. Economic geography, 2013,33(5):144-149.]
[16]KHAN A R. The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income in rural China[M]. UK: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93.
[17]邢鸝, 樊勝根, 羅小朋, 等. 中國西部地區農村內部不平等狀況研究――基于貴州住戶調查數據的分析[J]. 經濟學(季刊), 2009(1):325-346.[XING Li, FAN Shenggen, LUO Xiaopeng, et al. Inequality in western rural China:a household analysis in Guizhou Province[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09(1):325-346.]
[18]MENDOLA M.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a propensityscore matching analysis for rural Bangladesh[J]. Food policy, 2007(32):372-393.
[19]BECERRIL J, ABDULAI A. The impact of improved maize varieties on poverty in Mexico:a propensity scorematching approach[J]. World development, 2010,38(7):1024-1035.
[20]冒佩華, 徐驥. 農地制度、土地經營權流轉與農民收入增長[J]. 管理世界, 2015(5):63-74. [MAO Peihua, XU Ji. Rural land system,land management right transfer and farmer’s income increase[J]. Management world, 2015(5):63-74.]
[21]萬廣華. 經濟發展與收入不均等:方法和證據[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WAN Guanghu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inequality: methods and evidence[M]. 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ress,2006.]
[22]萬廣華. 解釋中國農村區域間的收入不平等:一種基于回歸方程的分解方法[J]. 經濟研究, 2004(8):117-127. [WAN Guanghua. Accounting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rual China:a regression based approach[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4(8):117-127.]
[23]高夢滔, 姚洋. 農戶收入差距的微觀基礎:物質資本還是人力資本?[J]. 經濟研究, 2006(12):71-80. [GAO Mengtao, YAO Yang. Which is the main reason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physical assets or human capital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6(12):71-80.]
[24]許慶, 田士超, 徐志剛, 等. 農地制度、土地細碎化與農民收入不平等[J]. 經濟研究, 2008(2):83-92. [XU Qing, TIAN Shichao, XU Zhigang, et al. Rural land system, land fragmentation and farmer’s income inequality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8(2):83-92.]
[25]f廣華, 周章躍, 陸遷. 中國農村收入不平等:運用農戶數據的回歸分解[J]. 中國農村經濟, 2005(5):4-11. [WAN Guanghua, ZHOU Zhangyue, LU Qian. Sour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rural household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5(5):4-11.]
[26]趙劍治, 陸銘. 關系對農村收入差距的貢獻及其地區差異――一項基于回歸的分解分析[J]. 經濟學(季刊), 2010(1):363-390. [ZHAO Jianzhi, LU Ming. The contribution of guanxi to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and a crossregional comparison:a regression based decomposition[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10(1):363-390.]
[27]SHORROCKS A, WAN G. Spatial decomposition of inequality[J]. Magnetic resonance in chemistry, 2004,48(2):91-93.
[28]ROSENBAUM P R, RUBIN D B. Reducing bias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using subclassification on the propensity scor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84,79:516-524.
[29]郭慶海. 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尺度:效率抑或收入[J]. 農業經濟問題, 2014(7):4-10. [GUO Qinghai. The measure of land proper scale management:efficiency or income [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4(7):4-10.]
[30]WAN G, CHENG E. Effects of land fragmentation and returns to scale in the Chinese farming sector[J]. Applied economics, 2001(33):183-194.
[31]TAN S, HEERINK N, KUYVENHOVEN A, et al. Impact of land fragmentation on rice producers’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southeast China[J]. Njas Wageningen journal of life sciences, 2010(57):117-123.
[32]GAO L, HUANG J, ROZELLE S. Rental markets for cultivated land and agricultural investments in China[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2,43(4):391-403.
[33]MORDUCH J, SICULAR T. Rethinking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with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2,112(1):93-106.
作者簡介:楊子,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土地經濟與政策、土地可持續利用管理。Email:。
[關鍵詞]市場結構;企業效率;績效
[中圖分類號]TP3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6-0063-02
1 模型的建立
當前學者在SCP范式中的市場結構和市場績效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分為了四個假說模型,包括傳統SCP假說、相對市場力量假說、X效率結構假說以及規模效率結構假說。
本文主要是根據Berger于1995年推導的以下回歸方程來檢驗以上的四個假設:
在上式中,π表示企業的績效變量;CONC表示市場集中度;MS表示市場份額;X-PTE表示X效率;SE表示規模效率;Z代表控制變量。
其中X效率主要是反映了企業依靠管理水平和生產技術生產產品的能力,該效率指標無法直接測出,所以本文通過DEA方法測得純技術效率來近似替代該效率。
通過模型方程式(1)再結合我國網絡游戲產業的實際發展狀況,可以建立模型方程式(2)來分析檢驗我國網絡游戲產業市場結構和績效之間的關系。
在模型方程式(2)中的被解釋變量π是表示企業績效變量,這里主要定義為資產利潤率ROA。
CR:市場集中度,本文主要為中國八個上市網絡游戲公司收入占總收入的比值。
MS:為單個網絡游戲公司銷售收入除以全國網游產業的總銷售收入。
X-PTE:X效率,如上文所述,本文將通過DEA方法中的BCC模型確定純技術效率代替X效率,投入指標為勞動力人數、企業資本總額、產品銷售成本,產出指標為總銷售收入和利潤總額。
SE:規模效率,解釋網絡游戲企業經營規模的變動給總成本帶來的影響,也是通過DEA方法中的BCC模型一同得出。
WA:文化產業產值增長率,該變量主要是為了檢驗我國網絡游戲產業與整個文化產業中的其他產業是否有相關性。主要由上年度的文化產業產值除以兩年間的產值差得出。
RA:銷售收入增長率,主要由上年度網絡游戲產業的總銷售收入除以兩年間的總銷售收入差得出。
ε:隨機誤差項。
本文研究樣本取自2005―2009年我國網絡游戲產業比較有代表性的八家上市公司,包括盛大、騰訊、巨人、網易、網龍、搜狐暢游、完美時空、九城,2005―2009年這些企業集團的年銷售收入均排在全國前10位,且總銷售收入占了本行業收入的80%以上。
2 模型判定的依據
(1)傳統SCP假說。傳統SCP假說認為市場集中度和利潤率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Stigier,1964)。當市場集中度系數大于0且顯著時,表明該產業支持傳統SCP假說。
(2)相對市場力量假說。相對市場力量假說認為市場份額和利潤率之間存在著顯著正相關關系,當Berger模型中市場份額系數大于0且顯著時,表明具有相對市場力量假說的特征。然后還必須證明市場結構變量(集中度和市場份額)和效率變量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Berger,1995)。這就需要對以下方程進行估計,此時效率變量作為被解釋變量。
(3)X效率結構假說。X效率結構假說認為具有較高X效率(純技術效率)的企業相對于競爭對手能利用較低成本獲得更高的利潤,具有低成本和高利潤優勢的企業會增加市場份額進而提高市場集中度。當回歸方程中其系數大于0且顯著時,說明X效率與利潤率存在正向相關關系,要想證明X效率(純技術效率)假說,還必須證明效率變量和市場結構(集中度和市場份額)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Berger,1995),這就需要對以下方程進行估計,此時市場結構變量作為被解釋變量。
(4)規模效率結構假說。規模效率結構假說認為具有規模效率的企業能夠以較少的成本獲得較高的利潤,這同樣可以擴大企業市場份額,使得市場集中度提高,當規模效率系數大于0且顯著時,說明規模效率與市場績效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要想證明規模效率假說,還必須證明效率變量、市場結構集中度、市場份額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同樣需要對方程式(5)和方程式(6)進行回歸估計。
3 模型的分析
通過SPSS16.0對樣本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到了模型方程(2)的結果:
從表1回歸結果可以看出:①市場集中度CR系數為負數,且該項T的顯著性檢驗為0.6894>0.05,并沒有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也就是說網絡游戲市場集中度對資產利潤率并沒有顯著的影響,這表明我國網絡游戲業拒絕傳統SCP假說。②市場份額MS的系數為正數,且該項T的顯著性檢驗為0.06>0.05,也沒有通過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但是卻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我國網絡游戲產業中的企業市場份額和市場績效之間還是存在一定的正相關關系,但是在本文前提假定必須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所以依舊認為我國網絡游戲產業拒絕相對力量假說。③X效率系數為正數,且該項T的顯著性檢驗為0.0240
X效率對資產利潤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不足以判斷我國網絡游戲產業存在X效率假說。驗證這一結論的可靠性,還必須考慮“效率結構”假說成立的必要條件,即方程式(5)和方程式(6)。如果方程式(5)中X效率系數為正數且顯著,或者方程式(6)中X效率系數為正數且顯著,就可表明我國網絡游戲產業X效率假說成立。方程式(5)和方程式(6)的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可以看出,在方程式(5)的回歸結果中,X效率的系數為正數,但該項目T的顯著性概率為0.859>0.05,沒有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可以認為X效率對相對市場集中度影響效果并不顯著。在方程式(6)的回歸結果中,X效率的系數為正數,該項T的顯著性概率為0.029
從上述分析可知,規模效率、X效率等因素會影響市場績效,但是市場集中度和市場份額并不直接影響市場績效,表明我國網絡游戲產業拒絕市場力量假說,支持效率結構假說。
4 結 論
據以上實證結果可得,我國網絡游戲企業績效主要來源于企業的效率,可能有以下幾方面因素:
(1)在對市場力量假說檢驗中,發現我國網絡游戲產業拒絕市場力量假說,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國較高的市場集中度并不是市場自發作用的結果,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來自于一些政策性壁壘,所以導致我國網絡游戲市場集中度雖然高,但卻并沒有對利潤率造成明顯的影響。
關鍵詞:高新技術企業;成本粘性;資本密集度;勞動密集度
一、 引言
目前,中外學者對成本粘性的探討越加深入。但是針對某一類型企業的研究幾乎沒有,特別是忽略了高新技術企業這一重要企業類型,高新技術企業成本粘性的存在性及影響因素將成為其成本管控的重要參考依據。因此本文將以高新技術企業作為研究對象,進行探索性的研究。
二、 研究假設與實證模型
1. 研究假設。理論認為,當高新技術企業的銷售業績降低時,高管并不會同步降低自己的工資。同時,為了避免其管理權限受到削減,會留有閑置資源供其備用配置。而當銷售業績超過預期時,高管們往往要求股東為其加薪。即,高新技術企業的成本并未隨著銷售業績增減變化而呈現對稱比例的增減變化。不完全契約理論認為,高新技術企業的管理層如果無法準確的預期成本的變化,當企業經營業績降低或低于預期水平時,成本就無法得到及時調整。交易成本理論認為,高新技術企業在進行資源調配時會產生費用,當經營業績降低或低于預期水平時,企業為了不產生預期之外的費用,則不會調整已約定事項,成本粘性就此產生。綜上,本文提出假設1:
H1:我國高新技術上市企業存在成本粘性。
當國家經濟快速增長時,企業管理層也會傾向于大興土木興建廠房,采購技術含量高的機器設備并引進相關技術,使得企業相關成本大幅增加。若此時企業的經營狀況驟然下降,短時期內處理閑置資源并不能達到降低企業成本的目標,此時高新技術企業就會表現出較大的成本粘性。相反,當國家經濟增速放緩甚至出現負增長,高新技術企業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會停止生產規模的擴大和新設備的采購,甚至會進行裁員,這種情況下企業表現出來的成本粘性就會較小。據此,本文提出假設2:
H2:高新技術上市企業在經濟繁榮期時的成本粘性比經濟低迷期時的成本粘性要大。
高新技術企業多為資本密集度較大的公司,當企業經營業績大幅降低時,對應的單位產品變動成本會發生較大數值的變化,因此資本密集程度大的高新技術企業成本粘性相對較大。同時,高新技術企業管理層進行資源配置時,會產生相應的調整成本。在以上兩個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成本粘性逐漸變得更大。相反的情況下,高新技術企業成本粘性會逐漸變小。據此,本文提出假設3:
H3:高新技術上市企業的成本粘性與資本密集度成正比。
高新技術企業往往重視研發環節,因此會在這一環節投入大量的人力與物力資本。當企業經營業績大幅降低時,對應的單位產品變動成本會發生較大幅度的變化。因此資本密集程度大的高新技術企業成本粘性相對較大;同時,高新技術企業管理層進行資源的調節配置時,會產生相應的調整成本。在以上兩個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成本粘性會變得更大。相反的情況下,高新技術企業成本粘性會逐漸變小。據此,本文提出假設4:
H4:高新技術上市企業的成本粘性與勞動密集度成正比。
2. 實證模型。本文基于Anderson(2003)和Subraman-iam與Weidenmier(2003)的關于費用粘性的LOG模型,建立以下系列檢驗模型。
通過模型(1)來檢驗我國高新技術上市企業是否具有成本粘性。
ln()=γ0+γ1ln()+γ2Di,t*ln()+εi,t(1)
模型(1)中:
Cost――成本;
Rev――營業收入;
i――樣本公司數量;
γ0――常數項;
γ1――營業收入上升l%情況下,成本變化的百分比;
γ2――成本粘性系數;
Di,t――名義變量,當t期的營業收入相對于(t-1)期營業收入是下降時,Di,t=1;其他條件下,Di,t=0。
模型(1)中,在營業收入上升一個1%時,成本上升γ1;收入下降1%時,成本降低(γ1+γ2)。在高新技術企業具備成本粘性的條件下,成本降低值(γ1+γ2)比成本上升值γ1要小,(γ1+γ2)
本研究把經濟趨勢分為二類發展時期,即經濟興盛期和經濟退步期,文中用Gt表示第t年GDP增長率。
模型2:ln()=γ0+Σ4aDa,i,t*ln()+εi,t(2)
模型(2)中:
D11 Gt
0 其他
D21 Gt
0 其他
D31 Gt>0, 且營業收入變化率
0 其他
D41 Gt>0
0 其他
a――名義變量指代的其中一種情況(i=l,2,3,4);
γ1――在Gt
γ2――在Gt
γ1+γ2――在Gt
γ3――在Gt>O的條件下,營業收入上升l%時,成本變化百分數;
γ4――在Gt>O條件下的成本粘性系數;
γ3+γ4――在Gt>O條件下,營業收入降低1%時,成本變化百分數。
模型(2)中,取γ2說明外部經濟呈負增長條件下高新技術企業的成本粘性系數,γ4說明外部經濟呈正增長條件下高新技術企業的相關成本粘性系數。γ2與γ4愈小,成本粘性數值(絕對值)會愈大。如果γ2>γ4,即可說明:國家經濟環境發展不理想情況下,高新技術企業成本粘性相對較小;國家經濟發展良好的情況下,高新技術企業成本粘性相對較高,即國家經濟環境發展狀況與高新技術企業成本粘性呈正相關的關系。
本文選擇資本密集度或勞動密集度的中位數作為界線劃分樣本數據,分別分析這兩組數據的高新技術企業成本粘性,效仿模型(1)建立如下模型(3)。
模型3:ln()=γ0+Σ4aγaDa,i,t*ln()+εi,t(3)
模型(3)中:
D11 資本密集度(或勞動密集度)>樣本
資本密集度(或勞動密集度)的中位數
0 其他
D21 資本密集度(或勞動密集度)>樣本資本密集度
(或勞動密集度)的中位數,營業收入變化率
0 其他
D31 資本密集度(或勞動密集度)
密集度(或勞動密集度)的中位數
0 其他
D41 資本密集度(或勞動密集度)
(或勞動密集度)的中位數,營業收入變化率
0 其他
a――虛擬變量指Di中的一種情形 (i=l,2,3,4);
γ1――當資本密集度(或勞動密集度)>樣本資本密集度(或勞動密集度)中位數時,收入增加1%時的成本變化率:
γ2――當資本密集度(或勞動密集度)>樣本資本密集度(或勞動密集度)中位數時的成本粘性系數;
γ1+γ2――當資本密集度(或勞動密集度)>樣本資本密集度(或勞動密集度)中位數時,收入減少l%時的成本變化率;
γ3――當資本密集度(或勞動密集度)
γ4――當資本密集度(或勞動密集度)
γ3+γ4――當資本密集度(或勞動密集度)
當高新技術企業資本密集度>樣本企業資本密集度中位數條件下,或勞動密集度>樣本企業勞動密集度中位數條件下,高新技術企業的成本粘性為γ2;當高新技術企業資本密集度
3. 變量的選取。
(1)成本變量。本文選擇主營業務成本、營業稅金及附加、銷售費用、管理費用和財務費用之和表示成本粘性中的"成本"。為了消除不同時期和不同企業數據方差過大對結果的影響,成本變化率用本期發生成本與上期發生成本比值的自然對數表示。
(2)銷售量增減變動。本文選擇營業收入的變動來度量企業銷售量的變動。同樣,營業收入變化率用本期營業收入與上期營業收入比值的自然對數表示。
(3)宏觀經濟環境。本文選擇用GDP增長率的變動方向來衡量宏觀經濟環境的走勢。
(4)資本密集度。本文采用高新技術企業總資產與營業收入的比值來度量企業的資本密集度。
(5)勞動密集度。本文采用高新技術企業應付職工薪酬與營業收入的比值來度量勞動密集度。
三、 實證分析過程及結果
1. 樣本及數據來源。本文以高新技術企業2008年~2013年披露的財務報告為基礎樣本的數據來源。篩選樣本的標準是:(1)剔除2008年以后上市企業,以保證樣本數據的完整性;(2)手工選取在2008年和2010年連續兩次被評為高新技術企業的企業;(3)剔除財務數據缺失的企業;(4)剔除成本變化率與營業收入變化率的絕對值大于3的企業。共有125家滬市A股的高新技術企業符合條件,樣本數據來自于CSMAR數據庫。
2. 樣本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樣本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1)收入變化率平均數13.56%,處于相對良好的增長狀況;成本變化率平均數是13.17%,即收入變化率相對較大。(2)資本密集度平均數是1.811 3,即平均總資產周轉率是一年1.811 3次。(3)勞動密集度的均值為0.087,可知其人力成本為0.087,即每一元收入的人力資本成本為0.087元。
3. 實證分析結果。本文選用SPSS21.0統計軟件對相關截面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實證結果見表2。
(1)高新技術企業具有成本粘性。γ2值是-0.081,營業收入上升1%條件下,成本上漲91.2%(即γ1);營業收入降低1%條件下,成本僅下降83.1%(γ1+γ2)。即銷售量增減變化數值相同的條件下,成本增加變化率(91.2%)高于成本減少變化率(83.1%),證明了假設1。
(2)高新技術企業成本粘性的客觀影響因素。(1)外部經濟呈負增長條件下成本粘性系數γ2=-0.060,當營業收入上漲1%時,成本上漲0.914%;當營業收入降低1%時,成本降低0.908%。外部經濟呈正增長條件下成本粘性系數γ4=-0.128γ4,這與假設2相吻合。(2)當資本密集度>樣本資本密集度的中位數時,成本粘性為γ2=-0.644,即當營業收入上漲1%時,成本上漲0.733%;當營業收入降低1%時,成本降低0.089%。當資本密集度樣本勞動密集度的中位數時,成本粘性為γ2=-0.541,即當營業收入上漲1%時,成本上漲0.801%;當營業收入降低1%時,成本降低0.260%。當勞動密集度
四、 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研究結果,本文提出以下四點政策建議。
1. 加強宏觀經濟調控。在國家經濟繁榮的條件下,應防止過度投資導致的成本回收壓力過大;在國家經濟不景氣的條件下,國家應防止高新技術企業為了迅速降低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而停止技術研發。
2. 加強高新技術企業的外部監督。外部對高新技術企業的監督檢查,有利于企業及時合理地調整資源配置,從而管控企業的成本粘性。
3. 提高高新技術企業高管的管理效率和管理能力。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很多,例如:通過培訓等方式,提高管理層的經營管理水平;倡導管理者的創新思維和國際視角等。
4. 合理控制企業的資本密集度和勞動密集度。一方面,要控制企業的資本密集度,不可盲目地只知投資,而不注意資本的回流;另一方面,在面對多變的經濟環境時,企業要合理控制人才的引進,從而達到控制勞動密集度的目的。
參考文獻:
[1] 孫崢,劉浩.中國上市公司費用“粘性”行為研究[J].經濟研究,2004,(12):26-34.
[2] 江偉,胡玉明.企業成本費用粘性:文獻回顧與展望[J].會計研究,2011,(9):74-79.
[3] 劉嫦,楊興全,李立新.績效考核、管理者過度自信與成本費用粘性[J].商業經濟與管理,2014,(3):78-87.
[4] 王文甫.價格粘性、流動性約束與中國財政政策的宏觀效應[J].管理世界,2010,(9):11-24.
[5] 崔學剛,徐金亮.境外上市、綁定機制與公司費用粘性[J].會計研究,2013,(12):33-39.
基金項目:吉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吉林省上市公司R&D投入績效提升對策研究:基于公司治理視角”(項目號:2014Bs50);東北師范大學哲學社會科學校內青年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基于低碳經濟視角的新能源汽車產業聯盟內外部運行機制研究”(項目號:12QN021)。